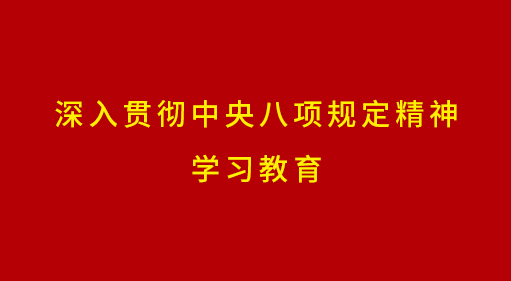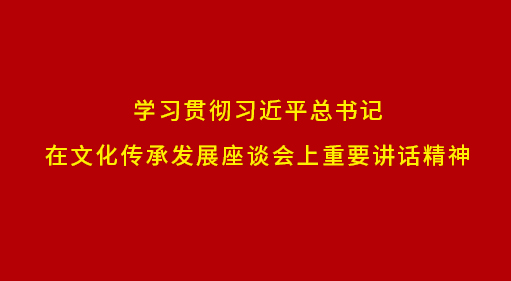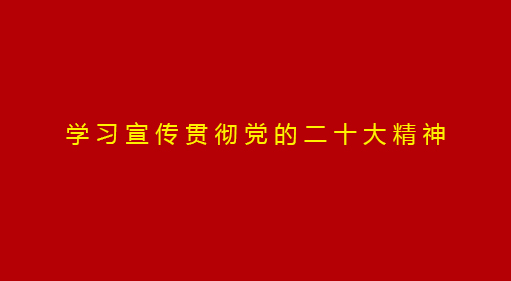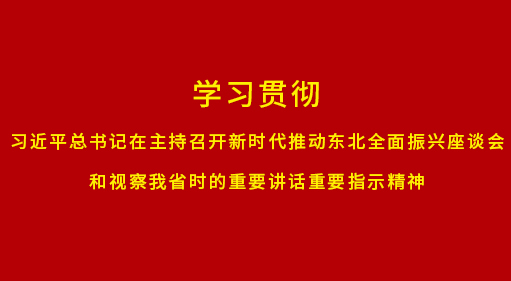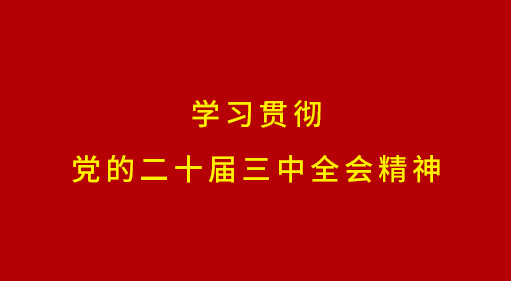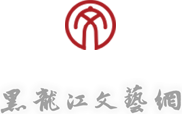类文本新视角:作为整体的网络文艺
时间:2025-07-22
刘国强
摘 要:网络文艺中的类文本展现出许多新质:网络小说内部的评论类文本散发着“现场”灵韵,视频中的文案信息具有模仿语义域的功能,起点中文网等网站的榜票排行成为一种特殊的“景观”。网络文艺中并不存在绝对的(正)文本或类文本,二者是相对而言,且是互涉共生的关系。在接受过程中,文本的内容通过话题、梗、名场面等形式被类文本化,即“文本类文本化”;类文本经过媒介的传播而转换为(正)文本,同时伴生对应的类文本,并且类文本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改造(正)文本,即“类文本文本化”。由此,类文本理论为网络文艺研究提供了一个内外兼顾、动静结合与互相指涉的批评角度。
关键词:网络文艺;类文本;“现场”灵韵;景观化
在网络小说阅读中,许多读者沉浸于作者构建的文学世界之余,也常常点开书中的评论,欣赏各地网友的精彩留言;在b站、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上,视频的封面、时长、文案、标签、播放量等信息,往往是吸引观众点击的关键因素。对于想选择一本“好书”阅读的读者,网络文学网站中的各类榜票排行,以及网络小说的类型标签、连载字数等,就是他们必须注意的细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评论、文案、榜票排行——无论是嵌入在网络文艺作品内部,还是散落在网络空间之中——都构成了网络文艺的“类文本”。如何理解新媒介的特性,怎么深入网络文艺的内部?类文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宜且有效的新视角。
一、从印刷到网络:媒介旅行中的类文本
从1997年法国学者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著作《门槛》(法语“Seuil”)被译为英文开始,国内外学界对类文本(paratext)理论日渐关注,至今俨然成为学术热点。随着媒介的发展,类文本也从纸媒进入影视、广告等领域。韦迪斯、皮格乃格瓦里等国外学者,赵毅衡、许德金、郭建飞等国内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新媒介中的类文本研究,例如皮格乃格瓦里提出的“类文本2.0”(paratext 2.0)[1]、赵毅衡提出的“伴随文本”[2]、许德金及其团队建构的“文本—类文本共生叙事”[3]等研究成果。然而,从实际情况看,这些理论有的无法完全适应中国网络文艺的现状,有的纸媒批评痕迹过于明显,目前虽有不少成果将类文本理论用于广告、影视、网络文学等领域,但多是简单地将纸媒语境里的类文本进行类比移植,对于网络文艺中的种种新媒介特性疏于体察与理解。
在热奈特早期的《广义文本之导论》《隐迹稿本》等作品中,已有涉及类文本概念,但直到《门槛》(1987)面世,热奈特才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学作品基本上由文本组成,文本最基本的定义为或长或短、或多或少有意义的语言表达序列。但是这个文本很少以未加装饰的状态呈现出来,即没有被一定数量的言语产物或其他产物加以强化和伴随,如作者姓名、标题、序言、插图。尽管我们并不总是知道这些产物是否被视为文本的附属物,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围绕并延展文本,准确地说是为了‘呈现’文本——使其呈现,以确保文本在世界上在场,确保它(至少在目前)以书的形式‘接受’与消费。”[4]在热奈特看来,类文本处于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未定义区域”,其首要意义在于“呈现”文本,简言之,使“书”以“书”的形态呈现,使“文本”以某种“文本”的形态呈现。
凭借类文本理论,热奈特打破了结构主义家们所强调的“封闭”文本,为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范式。对于类文本的定位,热奈特在《门槛》中明确将类文本视为“文本”的功能性辅助物,无论一个作品中的类文本如何出色,它永远只能附属于自己的“主人”——(正)文本。例如,著作中的各级标题、出版信息以及插图封面,或是书法作品中的序、跋、印章等,尽管在读者进行审美活动时,它们提供了诸如阅读导航、信息补充、文本阐释等重要作用,但在热奈特看来,其重要性都无法与(正)文本相提并论。对于二者关系,热奈特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没有类文本的文本就像没有赶象人的大象,失去了力量;没有文本的类文本则是没有大象的赶象人,是愚蠢的走秀。”[5]可见,在热奈特的理论逻辑中,类文本与文本之间最主要的关系是共生互补。
类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界限并非总是明晰的,而且热奈特也意识到类文本的适配范围也不应只局限于“印刷”文本。在《门槛》的结论部分,热奈特说道:“我也省略了三种实践,它们的类文本相关性在我看来是不可否认的,但单独调查每一种实践所需的工作量可能与整体处理这一主题一样多。”[6]随之热奈特提出了自己的展望:“如果我们愿意将这个术语扩展到不包含文本的领域,那么很明显,其他一些艺术,即使不是全部,也有与我们的类文本等同的东西:例如音乐和造型艺术中的标题、绘画中的签名、电影中的字幕或预告片,以及展览目录、乐谱序言(见1841年李斯特的《朝圣岁月》前言)、唱片封套和其他外围或外延的支持。”[7]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在全新理论视角的注视下,类文本进入媒介层面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果说热奈特对类文本理论的建构具有开创性,那么类文本在媒介文化研究中进一步地发展与应用,则要靠学界的持续探索。在上述学者中,与本文思路相近的是许德金团队的郭建飞,他倡导类文本的数字媒体研究视角。郭建飞“通过将类文本理论与影视作品及数字媒体研究相结合,推进类文本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拓展影视作品及数字媒体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畴”[8]。在具体实践中,郭建飞划分出具有叙事性功能和非叙事性功能的两种类文本,并细分出三种类文本与正文本的作用区别:一是类文本作用小于文本;二是类文本作用与文本同等重要;三是类文本作用大于文本。这种将本属于印刷文学的类文本,扩展到影视作品以及数字媒体领域的做法,显然意识到了类文本之于新媒介的兼容性,例如郭氏把影视作品的前后字幕、链接文本、数字光盘等,视为起着叙事功能的类文本,无疑为类文本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新视界。
值得进一步商榷的是,这种以纸媒中主要起着叙事补充功能的类文本,平行类比影视作品或新媒介中的类文本,继而为类文本与(正)文本之间的作用画上大于号、小于号与等于号的思路,是否默认了一个前提:影视作品、网络媒介中的类文本与印刷文学中的类文本,在数量形态、传播速度与实际功能上可以等量齐观。事实上,新媒介与传统媒介之间存在着诸多迥异,如网民权威、算法推送、评论互动、流量数据等。因此,有理由相信,网络媒介中出现的类文本由于新媒介特性的加持,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需要特别重视。
在网络媒介中,大众不仅被授权参与批评,还参与到了类文本的创作中,由此形成的类文本正无时无刻不对作者的作品进行“盗猎”与“挪用”,这与热奈特认为类文本可以确保“文本的命运”(text a destiny)与作者目的一致的功能已然不同。甚至由于网络上存在大量由网民参与生产的类文本,更使得“文本的命运”偏离了作者的原本意图。例如经典的影视作品被网友恶搞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既然类文本在网络上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异,那么再沿用叙事或非叙事来区分这些类文本就显得不合时宜,至于将类文本与文本进行作用比对,也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纸媒批评的旧习。
与其相信类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一条放之四海皆准的区分原则,不如认为在网络媒体中,类文本与文本的形态是相对而言的,不存在绝对的(正)文本,也不存在绝对的类文本。这可以为类文本理论提供一个更具弹性的应用空间。学者许德金将类文本的外延限制在相对封闭的固定空间[9],其成效是“缩小了副文本的外延,完全排除外副文本,也就割断了外部视角的可能性”[10]。与传统纸媒相比,“网络”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甚至是无限开放的空间,将类文本严格关押在某一封闭领域,实在与网络媒介的天性相违。
对于网络文艺而言,对类文本进行条分缕析式的定义、分类,进而计较某个作品属于类文本还是(正)文本,这种理论预设上的完全廓清并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某种语境中相对地区分出类文本与文本的界限,在此基础上,及时体认网络文艺中展现出的类文本新质,并讨论正文本与类文本二者在网络文艺中相互交融、转换与激荡的状态,从而为网络文艺提供更加贴切的理解与批评角度。
二、网络文艺中类文本的新作用
网络文艺中的类文本与纸媒文学中的类文本,在功能上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例如纸媒批评里类文本的阅读导航、叙事补充、解释引导、审美意义等作用,几乎可以平行移植来形容网络文艺中的类文本,然而,二者的相似只能说明网络文艺与传统文艺在某种形态观念上的相似,却无力解释网络文艺类文本出现的新质。在网络文艺中,类文本的新质及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现场”灵韵
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技术虽然让艺术作品能够广泛传播,但也导致传统艺术中“此时此地性”“本真性”“独一无二性”等审美特征的消逝。他以《浮士德》为例指出,即使是乡下最蹩脚的《浮士德》演出,也比电影版的《浮士德》更具价值,因为现场演出具有不可复制的“灵韵”[11]。
在网络文艺中,评论、弹幕、聊天等互动形式也赋予了文艺作品独特的“现场”性。网络文学网站中,伴随(正)文本出现的评论,如本章说、间贴、段评等,让读者在阅读正文的同时,只需轻轻一点,就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书友的即时评论。这种互动性极大地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例如目前正在七猫连载的《北派盗墓笔记》,其最热门的段评便是具有此时此地性的话语,“留个脚板印,证明我来过”,共获得1.3万的点赞。再如近些年大火的《十日终焉》《一剑独尊》《大奉打更人》等热门网络小说,除了其叙事风格受到读者追捧外,其独特的评论氛围也是粉丝们乐此不疲的上瘾诱因。事实上,评论互动并不仅限于网络小说。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那些令人捧腹的搞笑神评,以及在b站视频中飘过的有趣弹幕,都已成为当代青年观赏网络文艺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换言之,这些“评论”类文本实际上充当了“现场”互动的桥梁。
无论是评论的内容,或是“评论”形式本身,都反映出网友乐于在网络阅读空间中分享自己的即时心得。在大量的网络文艺类文本中,既有解释性评论,也不乏“玩梗式”解说,还充斥着吐槽、建议、玩笑等多样化的信息。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将此种类文本的出现认定为“文艺评论体系中出现了新的标准即网民权威”[12],或认为“针对社交媒体语境中文艺的新变化,文艺理论应走向交往诗学”[13],这些都是很好的网络文学理论的探索路径。这也从侧面证实了网络文艺中的种种评论互动,其实质是网友为彰显自身存在,而进行的一种建构“现场”的活动——读评论或写评论,获得的恰恰是某种“现场”的阅读体验——这种体验正是“灵韵”的别样阐释。不同于机械复制时代的单向度传播,加拿大传播学家洛根便将“新媒介”的特性首先定义为“双向传播”[14],在双向互动的新媒介环境下,读者可以随时走进新媒介中的“现场”。
如果说网络文艺与传统文艺在审美性上并无本质区别,那么,网络文艺中涌现的大量评论类文本则通过媒介性构造出全新的“现场”。这些评论类文本在“交互沟通”(现)与“场景塑造”(场)之间,营构出了属于数字时代的“现场”灵韵。如今,“现场”灵韵已经成为当今网络文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看评论与看正文几乎同样重要)。进一步来看,网络文艺的“现场”灵韵根植于新媒体的互动性与即时性,因此,网友们在阅读过程中的“交往互动”,也应当被纳入文艺批评的视野,成为网络文艺的一种审美质素。
(二)模仿语义域
除营造“现场灵韵”外,“类文本”在短视频中常常发挥着模仿新闻形态的作用。部分创作者通过“类文本”元素,如红色标语、大号字体等,改变了短视频原有的“虚构”语义,使其指向现实语义域。当前,在短视频传播中,虚构内容的真实化问题愈发严重。许多自媒体为了博取流量,不惜使用“摆拍造假”“移花接木”“以偏概全”等手段,在网络空间引发了诸多不良影响,严重扰乱了网络的清朗生态。
例如,2024年2月,网红“Thurman猫一杯”发布的“秦朗巴黎丢寒假作业”视频,就是典型的虚假内容伪装成新闻的案例。此类“新黄色新闻”[15]通过伪造事件、虚假传播,严重扰乱了公众的认知,引发了网络空间的不良风气。此次席卷全网的“秦朗丢作业案”,在生产、传播、发酵等过程中面目逐渐“真实”,网络文艺中的类文本不能辞其咎。这样的“新闻”并不是个例,近年来已经有不少文章对“新黄色新闻”提出质疑,如《“秦朗是谁”不重要,“新黄色新闻”泛滥很危险》[16]、《每天有7亿人在看“新黄色新闻”,技术竟是罪魁祸首》[17]。“新黄色新闻”大多有较强娱乐性,常常与网络文艺内容混杂,因而此类短视频一经传播,传播力不可小觑。
仿新闻类短视频的制作虽然简单,但几乎每一步都旨在营造一种现实感。其制作并不难,在新建视频时,随意输入文字内容,一般而言,视频上部是黄底黑字的主题信息,接着用红字信息进行评论或解释,中间部分标注时间、地点,下部则加上“声音来源”进行讲述。通过这些简单操作,一个看似“根正苗红”的“伪事件”便诞生了。然而,此类行为严重违背了新闻传播的基本伦理,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极大不尊重。
中央网信办在2025年的专项行动中明确指出,要“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打击摆拍造假、虚假人设、虚假营销、炒作争议性话题等问题”,其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强化信息来源标注、虚构和演绎标签标注”[18]。显然,整治短视频中的标注标签等类文本信息,其目的就是为了遏制虚假短视频的真实化倾向,维护网络生态的清朗与和谐。
网络短视频生成便捷,传播快速,其内容又紧跟热点话题,因而能够引人停留观赏。我们常常看到,一条短视频被各个平台切割、编辑后,以碎片化的形式流转于网络空间。这些短视频的效果呈现——内容是真实还是虚假,风格是严肃正经还是插科打诨,总体上是保真或是失实——都与类文本的“模仿”能力紧密相关。文艺批评必须对这种“类文本”的滥用行为保持高度警惕,致力于揭示其潜在的误导性,同时为网络文艺注入积极的引导力量。这不仅是对网络生态的维护,更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坚守。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必须回归真实、回归价值,否则将失去其应有的生命力。
(三)制造“景观”
在媒介时代,“公众关注度”成为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有价品,“景观”的制造也因此成为文艺领域新型权威崛起的关键。如今,“景观化”无处不在,正如考夫曼言,“这些媒体系统影响了整个文学创作链,或更笼统地说,影响了整个知识生产链:从作家的形象到文学‘圈’(milieu)的形成,然后再到读者的阅读方式”[19]。对于读者来说,他们对网络作品价值的判断,很少受制于文学界的专业批评,而往往听信于畅销书榜单、网络热搜等“景观”因素。
网络文艺凭借其丰富多样的类文本,在各平台以不同方式制造能够获取公众关注度的“景观”。随意打开一个网络文学网站,很难不被网站上各式各样的排行榜、推荐等信息吸引。以起点中文网为例,其“景观”大体可以分为横、纵两种吸睛布局:横向布局包括“分类”“排行”“三江”“剧场”等栏目;纵向布局则涵盖“畅销精选”“主编力荐”“新书强推”等板块。具体到某部小说,该封面的类型标签、连载字数、火热程度等信息都变为了可视化、可量化的数据。浏览网络文学网站,就如同在逛一个被精心布置的文本超市,读者最后想要选取的作品,类似于被放置在超市货架前排的商品,因为其更容易被大众所关注和选择。
同样,一部作品火热程度也可以通过“景观”直观地体现出来。例如,2020年3月15日在起点上架的《大奉打更人》,在一个月内便获得八万张推荐票,并登上起点首页的编辑文字推,走红至今。再如七猫网站的《太荒吞天诀》《剑来》、晋江文学网站的《重回老板年少时》等网络小说,都是“榜上”有名的当红作品,其走红的证据便是“月票”“必读票”“出圈指数”等庞大的数据景观。相反,若一部小说刚开始连载就反响平平,无法大量获得“收藏”“推荐”“月票”——即无法获得类文本要素进而被“景观化”,一般情况下,也就意味着该小说的生命周期可能会提前终结。因而考夫曼说“书本就像酸奶一样会过期”[20],其实并非夸张。
网络文艺出于商业利益的目的,必须最大限度地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在此情况下,一部作品的公众关注程度往往与作品的“质量”成正向相关关系。网络文艺的景观化趋势,正是以关注度为最终追求的。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何网络文学网站要设置如此详尽的类型分类、榜票排行,其目的就是想通过类文本景观,帮助用户在最短时间内做出阅读的选择。网络文艺似乎遵从一个新法则:一部好的作品不一定被纳入“景观”,但无法被纳入“景观”的网络作品一定不是好作品。如果说网络小说与纸媒小说的重大区别在于媒介传播的不同,那么显而易见,新媒体的特殊形式使得网络小说呈现出独特的“景观”盛况,也形成了新的评价标准。在这种背景下,“类文本”便成为网络小说批评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维度。
三、整体观:互渗的“文本”与“类文本”
将类文本理论引入媒介领域,可以在兼顾(正)文本与类文本的基础上,对网络文艺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原因很简单:单纯对小说文本做出静态式的解读,或仅从网络性角度进行追踪,都难以公正、全面地获知某部作品得以火热的综合质素。因此,小说的内部研究以及小说携带的媒介性探索同样重要。在网络文艺研究中引入类文本理论,不仅有助于理解作品的传播机制,还能为建立更加科学的网络文艺评价体系提供理论支持。具体而言,类文本理论能够为网络文艺批评提供一个内外兼顾、动静结合与互相指涉的整体性研究视角。
作为整体的网络文艺,其类文本不仅在数量、质量与形态上发生了巨变,而且(正)文本与类文本之间也产生了诸多基于新媒介特性的关涉与互动,这种互动的典型特征表现为“文本的类文本化”与“类文本的文本化”。所谓的“文本类文本化”,主要是指(正)文本在接受者的接受过程中,其内容以话题、梗、名场面等形式被类文本化。换言之,接受者的关注重心正逐渐从(正)文本转向其衍生出的类文本。
在“现场”灵韵所生发出的狂欢氛围中,(正)文本被拆解为各种要素,成为“现场”灵韵的组成部分,并构建出“现场”语境。比如,历史剧《雍正王朝》的高潮部分“八王议政”播放时,正片的故事内容被观众拆解为一个个“包袱”(弹幕)。网友调侃雍正皇帝的扮演者唐国强“诸葛亮即将舌战群儒”,也有不少游戏比喻“开团”“敌方英雄已选中”,还有对野史的讨论如“哪来的血滴子,武侠看多了?”网友或搞笑、或较真、或调侃的评论并非企图对影片进行专业性点评,而是为了在你来我往、说说笑笑的集体讨论中营造“在场”感。网友们能够借“题”发挥,各显神通,正是因为影片所提供的文本语境给予了他们发挥的空间。正如麦克莱恩对“门槛”理论的补充:“这个框架是一种手段,它将目光拉到画面中来,将读者引入文本之中,是通向唯我世界的钥匙;当然它也可能会故意引开读者的视线,鼓励读者将注意力集中于语境而不仅仅是文本之上。”[21]当(正)文本化身为语境时,类文本内部的“群情激荡”证明,静观接受固然是一种欣赏姿态,但集体讨论中的“激情四射”,也成为观众喜闻乐见的环节。
相比较作为线性叙事的影片剧情,如今网友们更倾向于关注影视中的有趣片段,而评论往往容易在这些“名场面”周围集结。在b站播出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具有9千万的播放量,在评论区中,其中一条热门置顶的评论就是对这部影片名场面的详细总结,如“精灵副将马国成(田文镜,我xxx)第4集24:10;第一巴图鲁,第八集35:21;有德之人第9集35:44……”这些“名场面”出现时,大量弹幕随之涌现,成为关注互动的高潮部分。如果将文艺内容视作可供大众消遣的“话题素”,那么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文艺内容的话题化”[22]。在这种趋势下,网友可以肆意“甩包袱”“玩梗”,而影片中的“名场面”不仅是网友“包袱”的爆发点,还是短视频平台传播的“流量”片段。在b站、抖音、快手等软件上,形成了大量有关《雍正王朝》的“名场面”,而“名场面”又衍生出许多热“梗”。许多年轻人正是通过这些类文本,才对《雍正王朝》兴趣大增,大量的关注使这部25岁的老作品焕发新活力。不难发现,网友从(正)文本挖刨出的名场面、话题素,一方面意味着(正)文本被分解为类文本在互联网上传播;另一方面,这些片段化、包袱化的类文本得到广泛传播后,成为网络“景观”,并吸引来大量的公众对原片的关注。这种现象不仅改变了观众的观看习惯,也重塑了经典作品的传播路径。
文本的类文本化不仅出现在影视领域,网络文学、直播、游戏等文艺形式中也随处可见,但我们不能由此认为文本的类文本化是一个单向度过程,进而总结出类文本作用有大于(正)文本的趋势,反之亦然。关键在于,类文本与(正)文本之间并非是作用大小的关系,而是相对独立,但又相互指涉、渗透的,因而类文本的文本化,也是网络文艺中不能忽视的重要现象。
类文本文本化是指“类文本”指向“文本”的趋势。从形式上看,类文本可以通过媒介传播而逐渐转换为(正)文本,并伴生对应的类文本。例如,当电影《抓娃娃》的官方团队在抖音平台制作并发行电影宣传花絮后,该花絮与电影本身便构成了类文本与(正)文本的关系。然而,对于花絮而言,短视频中的文案、标题,以及点赞、转发、收藏等数据,以及网友的评论互动,又可以作为该花絮的类文本。截至2024年7月13日,抖音平台《抓娃娃》官方团队发布的45条花絮中,有七条点赞超过了一百万。高赞评论主要集中在“剧情讨论”与“影片态度”两类。其中一条花絮视频的文案标题为:“不要小瞧身边穿着朴素的人”,下方的黄字为“他们毛坯的人生很可能是假的”,这种剧透性质的文案在评论区引发了大家对《抓娃娃》剧情的好奇;此外,点赞较多的另一评论是“只要是他俩演的,就算是拍出了一个翔我也得尝尝是咸是淡”,类似言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点赞高,基本表明观众对沈马组合(沈腾、马丽)的期待,这也是影片宣传的最大卖点。由此可看出网友们对影片《抓娃娃》的兴致很高。作为研究者,不仅要观看影片的类文本,还要把握“类文本的类文本”,即学者赵毅衡所说的“文本的文本”[23],实际上,这是类文本经过传播后,具备了一定的独立叙事功能,因此类文本被“文本化”了。
类文本指向文本还意味着类文本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改造(正)文本。网络小说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证。与传统书籍不同,网络小说的创作与接受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作者日更几千字,读者便日读几千字。在网络小说阅读中的原生评论,除了可以构建“现场”灵韵,它们还是作者创作的重要依据。网友在评论区展现出对书中人物的爱憎以及对剧情的讨论,甚至“玩梗”等行为,都会被作者不同程度地纳入写作蓝图。本为附属性质的类文本便能够“登堂入室”,最终被改组为(正)文本,有学者将这种“众筹写书”“抄书评”“攀科技树”的写作过程称为“维基百科式的联合生产模式”[24],实际上,这便是类文本转换为“文本”的一个具化表现。
网络文艺的类文本营构了消费的狂欢氛围。以“现场”的互动吐槽、戏谑调侃,短视频的文案标题以及“景观”中的量化数据为代表的类文本,已经沁入网友对网络文艺的整个接受过程中。“文本类文本化”与“类文本文本化”意味着网络文艺的容量将大大增加,并且在网络文艺内部形成了互指互涉的动态轨迹,由此“作为整体的网络文艺”不仅在接受形态上成为可能,而且也为新时代的文艺批评指明了新的努力方向。
结 语
需要注意的是,网络文艺中的“文本类文本化”与“类文本文本化”现象也存在不少局限与弊病。在“文本类文本化”的过程中,正文本被分解为话题、梗、名场面等形式,虽然增加了互动性和传播性,但也可能导致文本的碎片化。《雍正王朝》《红楼梦》《西游记》等经典老剧虽获得新一轮关注,可碎片化的“名场面”可能削弱读者对正文本整体叙事和深度内涵的理解,导致读者的阅读体验只能停留在娱乐表面。另外,正文本的审美价值也有可能被类文本的娱乐性所稀释,弹幕和评论中的戏谑调侃容易分散接受者对正文本艺术价值的关注。对于“类文本文本化”而言,在商业资本与粉丝欲望的驱动下,类文本的过度介入很可能干扰正文本的叙事节奏和艺术表达,导致网络小说等网络文艺的创作携带过多的读者欲望,从而偏离其原本意图。
基于上述现象,网络平台需要建立类文本内容的筛选和审核机制,过滤掉低质量、误导或有害的类文本,以提升网络文艺中类文本的整体质量。同时,平台应通过教育与引导用户,提高用户对低质量类文本的拒绝意识,并鼓励用户生成高质量、有价值的类文本。从理论方向来看,可在“文本类文本化”与“类文本文本化”互涉共生的基础关系上,引入“动态平衡”的期待视角。在正文本与类文本的互动过程中,应强调二者的良性互动,避免一方对另一方的过度干扰,保持二者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和互补性。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正文本与类文本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推动网络文艺健康、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事件理论视阈下的中国网络文艺批评研究”(项目批准号:22AA001)阶段性成果]
[1] Pignagnoli V.Paratextual Interferences: Patterns and Reconfigurations for Literary Narrative in the Digital Age.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 for Cultural Narratology (AJCN). 2016;N.7 & 8(Autumn 2012/2014):102-119.
[2] 赵毅衡《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文艺理论研究》2010 年第 2 期。
[3] 郭建飞、许德金《从共生叙事到叙事共同体的文本—类文本共生叙事诗学构建——许德金教授访谈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4][5][6][7] 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JANE E. LEWI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p.410,p.405,p.407.
[8] 郭建飞《影视作品及数字媒体文本——类文本共生叙事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第6期。
[9] 许德金《类文本叙事:范畴、类型与批评框架》,《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0]聂家伟《国内副文本理论引介与批评综论》,《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4年第2期。
[11][德]瓦尔特·本雅明《艺术社会学三论》,王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12]胡疆锋、刘佳《云中漫步还是退而却步——论社交媒体与文艺评论的转型》,《中州学刊》2022年第4期。
[13]黎杨全《走向交往诗学:弹幕文化与社交时代的文艺变革》,《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14][加拿大]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
[15]“新黄色新闻”是指在短视频平台上出现的一种低质量、虚假、煽情、娱乐的资讯类视频,其特点是格式非常统一,封面上挂着黄底黑字、镂空红字的标语。参见拆台本尊《算法正在谋杀新闻,十亿中国网友却为此狂欢》,微博网2023年2月27日,https://monojson.com/s/pyq0l。
[16]《“秦朗是谁”不重要,“新黄色新闻”泛滥很危险》,央视网2024年02月20日,https://mp.weixin.qq.com/s/guna4M0ZluDNk5FlJlFlyQ。
[17]陆鹏鹏《每天有7亿人在看“新黄色新闻”,技术竟是罪魁祸首?》,《新京报传媒研究》2023年4月12日,https://monojson.com/s/9nD1e。
[18]《中央网信办发布2025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整治重点》,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2025年2月21日,https://monojson.com/s/bsSd1。
[19][20][瑞士]樊尚·考夫曼《“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李适嬿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第26页。
[21]转引自蔡沛珊《解释“门槛”:类文本理论的发展与应用》,《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22]黎杨全《从审美性到交往性:社交媒体语境下文艺批评的范式变革》,《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2期。
[23]赵毅衡《文本内真实性:一个符号表意原则》,《江海学刊》2015年第6期。
[24]黎杨全《走向活文学观:中国网络文学与次生口语文化》,《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