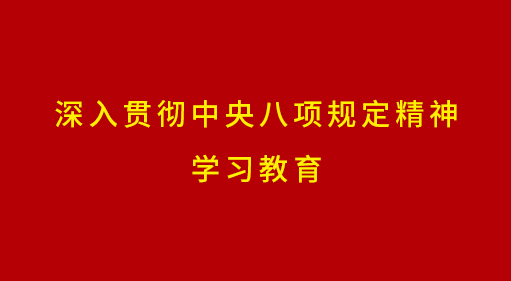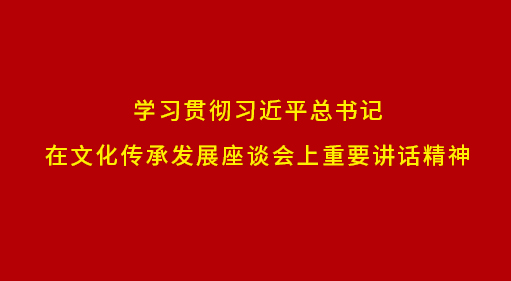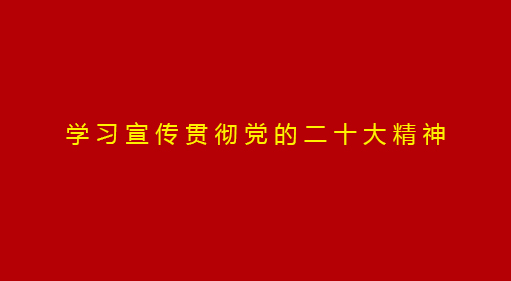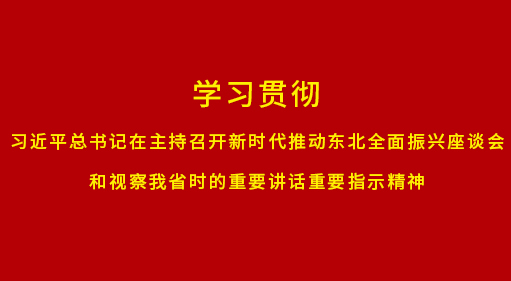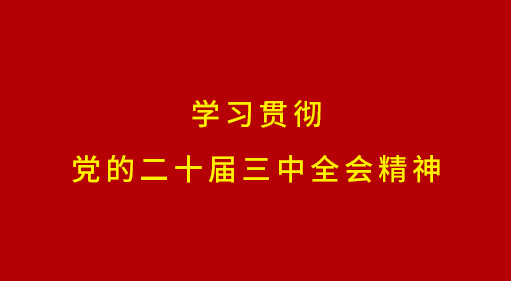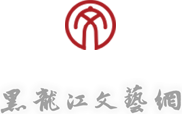解构与重构: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叙述视角探析
时间:2025-10-31
潘倩文
摘 要:影视解说活动伴随着影视艺术的诞生和传播同步兴起并发展。全媒体时代,具有“短”“平”“快”传播特征的影视解说类短视频为大众打开影视快餐大门,满足大众在碎片化信息时代进行影视鉴赏的需要。影视剪辑、生成式人工智能等软件使用方式的优化,为自媒体博主解构影视作品与生产短视频提供新质生产力。当下,AI语音合成技术、AI生成解说文本赋能短视频,促使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第一人称”心理独白的叙述模式产生,由“外视角”向“内视角”演变,在丰富影视解说类短视频解说形式的基础上,却也引发一系列生产与传播问题,因此,其叙事模式、审美意义以及传播弊端亟待讨论。
关键词:AIGC语音合成;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内视角;外视角
自2020年被定义为“视频化社会”元年以来,视频化信息作为当下最常见的传播形态,口语化、可视化信息特征日渐凸显。短视频平台作为当下拥有最广泛用户群体的网络场域,短、平、快的影像传播特征正在重塑大众影视审美的注意力与思维能力。从“倍速观看”“慢电影”“慢综艺”等新名词的提出来看,即可感知到当下大众思维的变化,在大众倍速观看影视艺术的背后,可以窥见到大众对于密集信息、有效率获得信息的强烈诉求,因此伴随着短视频媒介形式的兴起,影视解说短视频无疑成为全媒体时代的另一影视鉴赏方式。
叙述视角指观察与解读故事的视角,自影视解说类短视频诞生以来,从何种角度叙述影视故事是此类型短视频创作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AIGC技术全面赋能短视频生产范式,许多自媒体博主已具备AI语音合成技术、AI解说文本生成的媒介素养,并通过“克隆”影视作品中人物的音色特征,以某一角色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解说影视类短视频得到井喷式生产与传播。基于叙述视角的转换现象,得以窥见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在AIGC生产机制、媒介素养等层面显示出迅速发展的现象与弊端。
一、影视解说活动的媒介沿革
影视解说这一形式并非新媒体语境的产物,关于影视解说形式可以追溯到无声电影时期,这一时期已形成固定的放映解说形式、解说职业等。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影视解说形式以新媒体短视频形态传播,影视解说类短视频是以影视作品为创作素材,经过自媒体博主剪辑后配以口语解说的短视频形式,表现为自媒体博主对原影视作品情节逻辑的解构与重构,尽管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在当下已成为大众了解影视作品的重要渠道,但影视解说形式在我国传播媒介历程中均有所体现。
(一)无声电影时期的解说活动
新媒体语境下,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已成为帮助观众快速了解影视内容的主流视频形式。然而,影视解说并非新媒体时期的产物,这一形式可以追溯到中国无声电影时期。电影作为西方舶来品,在进入中国后各电影院为提升中国电影观众的观影体验,在电影放映过程中配备电影解说员现场解说电影情节,或为不识字的电影观众朗诵字幕,抑或模仿片中人物口型为人物对白配音,构成了电影解说、配乐与电影字幕之间互动的放映形态。张一玮指出:“20世纪初,早期默片依附于教会、学校和其他场所的中国电影放映空间,其间出现了以传教、教学或商品推销为目的的电影解说员,他们将默片放映和幻灯片演讲等形式结合起来,通常承担了宗教观念、科学知识和商品形象等方面的传播任务。”[1]另外,日本是较早开展电影解说活动的国家之一,在无声电影放映时期,日本电影放映活动衍生出较为正式的解说形式,并出现“活动弁士”一职,即在电影放映过程中,站在电影幕布前承担电影解说、角色配音的人,他们能够掌握多种音色,从而在现场完成对无声电影中不同角色的声音表演,此外,弁士可以随意调节电影播放速度,对于默片电影的声音表现与传播起着重要作用。“明治29年(1896年)11月25日,在日本神户神港俱乐部第一次公开放映电影时,便有讲解人这一司职”[2]。20世纪后日本大量进口欧美电影,弁士日益流行起来,已经成为日本观众观影时一同欣赏的重要表演活动。“根据1920年的一则警方记录,当时东京地区的注册活弁中有750名男性,90名女性。”[3]例如,日本电影《默片解说员》即以此段电影发展历史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俊太郎从小热爱电影,并一路成长为一名具有个人表演风格著名弁士的故事。影视解说形式在无声电影时期已在各国兴起,并成为一种解读外国电影、配音本土电影的重要形式。可见,默片时代各国对电影开展解说活动之普遍。
(二)电视传播时期的电影宣传
影视解说形式在新时期之所以萌生,源自20世纪90年代电视作为主流大众传播媒介对电影的解说与宣传,彼时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大众对于审美娱乐需求也不断提升,相对应的,对电视所播出的电影在内的文艺资讯需求量也有所提高。其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998年电影频道CCTV-6《佳片有约》、2006年《爱电影》《光影星播客》、2015年的《电影全解码》与2016年的《今日影评》等栏目,以及2004年科教频道CCTV-10的电影评论栏目《第十放映室》等,对时下热门电影进行解说或评价,为大众了解电影、鉴赏电影提供了信息窗口。此类影评类电视栏目一经播出,便因其短时间内述说电影故事的形式获得较高收视率,吸引各级电视台纷纷效仿。伴随着电视与网络媒介的交融,《电影全解码》《今日影评》等电影评论栏目也借助新媒体传播,寻求最广泛信息传播渠道,为大众提供鉴赏电影的审美方法与影片知识。
作为电视占据主流传播媒介时期大众观看电影解说的渠道,电影评论类电视栏目承担着该时期介绍、宣传、鉴赏电影的职能,主持人或特邀嘉宾在讲解电影情节内容的基础上,以电视为主流传播时期最具时效性的方式讲解电影故事以及宣传国内外电影资讯。以《第十放映室》“世界经典系列电影巡礼2——国产系列经典”一期为例,该期选取《一代宗师》《叶问》《师父》《战狼》等多部动作电影,对各部电影中的重要情节片段、代表性片段进行混剪,并采用画外音形式解说电影画面内容,在有限的解说篇幅内,完成对该电影中重要的情节、镜头语言、主题立意及该电影与其他电影对比的解说任务。不难看出,电影评论栏目是电视时期电影解说形式的具体表现,区别在于,电影评论栏目邀请电影专家、官方制作团队进行电影解读,尽管是以通俗形式对各电影进行解构与主题拼贴,但是相较于影视解说类短视频解说的内涵深刻程度,电影评论栏目仍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与教育性。
(三)新媒介传播时期的影视二创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以往处于被动观看的影视“接受者”“消费者”身份,转变为“生产者”,互联网“去中心化”“拼贴”等文化特质在诸多影视粉丝对影视作品进行二次创作现象中体现出来。2006年,自媒体博主“老湿”将电影《无极》剪辑成一条名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20分钟解说视频,以博主个人视角进行了电影故事的解构与重构。
伴随着用户生产内容(UGC)在互联网场域的不断下沉,以及短视频视听形式的普及,网民媒介素养的提升与短视频创作生产门槛的降低,诸多网络用户开始学习剪辑影视作品,具备一定影视作品混剪、影视作品解说等视频内容生产的媒介素养,以哔哩哔哩视频网站的影视解说类视频博主“刘哔电影”“哇萨比抓马”“假装讲电影”等为例,他们依据自身对该部影视作品的理解,尝试在10~50分钟内建构起以第三人称的情节转述,并对影片故事的历史背景、创作背景进行介绍,这是具有一定的影视专业性与个人风格的解说形式。
(四)新媒介传播时期的影视速食
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网络移动客户端不断革新,智能手机的发展与普及,使大众对于影视鉴赏、影视信息的获取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介、网络媒介所提供的观赏渠道,而纷纷转向移动新媒体的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也就是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所提出的“新新媒介”(New New Media)。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由三分钟内的影视作品画面、口语化解说词、背景音乐三部分构成,自媒体博主通过完整讲述影视故事的主线情节,使短视频用户能够了解影视作品的情节大意。相比于电视影评栏目重评论轻叙事的讲述特点,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则以概括情节为主,体现为重叙事轻评论特点。因此,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相较于网络影视解说视频,由于其时长较短,需要使用网感语言与快节奏剪辑使短视频用户快速沉浸至解说情节中。短视频平台的崛起,为影视解说类短视频提供了最广泛的受众群体,但也因短视频时长较短,用户浏览时间长,所形成产出与接受不匹配的问题。相对应地,短视频平台也催促此类自媒体博主加速生产短视频,并尝试在叙事模式、叙事视角、叙事节奏等层面进行创新,以解决创作端生产力不足的问题。
由此可见,影视解说形式伴随着电影诞生就已出现,并在传播媒介交融发展的历程中不断演化,显示出电视、互联网新媒介、新新媒介等不同媒介解说的文化特性。需要指出,在影视解说形式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影视解说短视频在数量与生产方式上与传统形式形成较大的区别,AIGC技术的赋能,促进诸多自媒体博主在叙述视角的选取与解说文本的生成层面拥有更加广泛的选择,而这正是当下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叙述视角多样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叙述视角建构
叙述视角即看事物的眼光与角度,“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4],在叙事学理论研究与文学、影视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内容为影视作品的情节介绍,其叙述视角通常由短视频博主群体构成,表现为外视角叙述。AI声音合成技术的成熟,促使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博主在创作时,选择影视作品中某一人物内视角,由剧中角色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事,从而实现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叙事视角及其解说文本的转向,此两种解说视角的侧重点也存在较大差异,正如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所言:“所谓视角是从作者、叙述者的角度投射出视线,来感觉、体察和认知叙事世界的;假如换一个角度,从文本自身来考察视角所及处的虚与实、疏与密,那么得出的概念系统就是‘聚焦和非聚焦’。”[5]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叙述视角即廓清聚焦类型的问题,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叙述话语》中指出三大类聚焦模式,分别为“零聚焦”“外聚焦”“内聚焦”,用以讨论文学作品中叙述视角与作品人物的关系。“零聚焦”即无固定观察角度的叙述,叙述者了解的内容比人物角色知道得多;“外聚焦”即叙述者从外部观察人物活动,了解的内容与人物角色一致;“内聚焦”即叙述者仅说出某一人物角色了解的情况。在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叙述视角中,外视角承担着“无聚焦”与“外聚焦”的聚焦类型,内视角则承担着“内聚焦”类型。正如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指出“解读文本是件复杂的工作,而大众文本的复杂性既在于它的使用方式,也在于它的内在结构”[6],影视解说短视频的叙事方式与结构显然依据叙述者视角呈现出外视角(第三人称)与内视角(第一人称)的鲜明差异。
(一)外视角:影视作品情节逻辑的戏仿
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外视角即第三人称视角,也可以称之为全知视角或全知叙述者,“全知叙述者不是故事中的人物,无论他/她/它叙述的是人物的内心活动还是外部言行,他/她/它的观察位置一般均处于故事之外”[7]。通常来看,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外视角即多以自媒体博主为叙述者,自媒体博主通过解说文本配以相对应的影视情节片段,建构起短视频解说情境。外视角叙述方式表现为叙述者与影视故事有一定距离感,能够较为全面、相对客观地叙述人物关系与情节发展,以便短视频用户能够借助博主的讲述抓取关键信息,建立起对该部影视作品的基础认知。
在外视角影视解说类短视频中,叙述表现为“零聚焦”与“外聚焦”两种形式。第一,表现为“零聚焦”类型的影视解说类短视频,通常能够形成夹叙夹议的解说形式,并融入解说者对该影视作品的看法与评价。在表现形态上,零聚焦类型以自媒体博主口语解说词、影视片段、背景音乐结合,形成先解说后评论的影片解说模式,解说文本融入博主的影视专业理论、影视观点以及电影、电视剧的情节背景,并在解说短视频结尾处对电影进行集中立意评论。显然,零聚焦类型显示出自媒体博主鲜明的解说风格与明确主题,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商业解说模式,影视片段的选择、背景音乐的选择均围绕原影视作品题材进行相应主题的解说创作,如音乐Fight用于悬疑题材解说、《广寒宫》用于穿越题材解说、True用于成长题材解说,等等。譬如,自媒体博主“椒盐说影”在解说国产影片《孙子从美国来》时,在短视频最后阐述了该电影的叙事逻辑与情节设计,以及其对该电影社会价值的评价。此种叙述方式不仅让短视频用户明确影片讲解结束,从解说氛围中抽离,并且能够使短视频用户对影片的感受与解说者的评价达成对接,从而获得对自我内心价值观肯定的满足感。另外,博主“布衣探案”在解说电影《红高粱》时,在解说开头增加电影《红高粱》的拍摄背景介绍,解说完该影片故事情节内容之后,在结尾介绍《红高粱》戛纳放映时的具体情况,此种叙述方式能够使短视频用户在了解影片故事的基础上对该电影创作、发行亦有所了解。由此看来,外视角中叙述者零聚焦的类型,更多的是强调自媒体博主对电影的认识,这种情况下,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已经成为约翰·费斯克所谓的“生产性文本”,是由自媒体博主编码后的影像文本,是与原影视作品形成互文关系的新影像文本而非原影视作品。
第二,表现为“外聚焦”类型,即纯客观叙事模式,作为叙述者的自媒体博主仅描写影视情节,不对情节与人物作出主观解读。例如,自媒体博主“星星动漫”解说欧美动画时,解说词为:
老人把家里仅存的粮食喂给了窗外的小鸟,小鸟在酒足饭饱之后竟变成了七个小矮人,为了报答穷困半载的老爷爷,小矮人趁着夜色偷摸着溜进老爷爷的鞋铺,仅用半个小时便将卖不出去的高跟鞋雕刻成了奢侈品。
此短视频仅从外视角对影视画面进行内容描述,既没有阐释影视作品中人物行为动机与情节走向,也没有对影视作品的主旨立意、故事背景进行评论。再者,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的影视解说类短视频中大量使用网感语言,形成诸多类似原始口语社会口语传播的套语模式,如“这个男人叫小帅,这个女人叫小美”等。而为了帮助短视频用户快速进入影视情节,对于影视人物称呼多则以性别或职业划分,从而达成对主要人物的认识,如“男人”“女人”“小帅”“小美”“大壮”“胡子哥”“金发妹”“服务员”“福伯乐”等,帮助短视频用户从外视角进入叙事情境,快速建构起对该部影视作品的全面认知。此外,影视作品情节分为主线情节与支线情节,外聚焦类型的另一形式为“原影视作品情节+字幕解说”结合的模式,通常表现为保留主线情节内容的影视原声,以逐帧画面字幕的形式,对影视情节、人物动作等影像深层含义进行描述,从而达到辅助短视频用户理解影视情节内容的效果。例如,在自媒体博主“优酷电影”解说《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中,选取女主江宁犯罪行为情节线为叙述脉络,保留原电影对白叙事,在画面中辅以女主犯罪动机字幕形式的解说文本以解说情节内容。同样,自媒体博主“传奇88”影视解说短视频中也采用此模式,其在解说《猎金·游戏》时使用字幕:
实习生来面试,一个小时前在厕所遇到投资大师,没有任何背景,打电话给副总裁,推荐他去其他公司,看到大师的研究公式,开始对他有好印象,给飞机公司做评估,来真的了,留下他,安排了很多事情,对徒弟很严格,小伙联系到了大公司,给徒弟机会锻炼锻炼,对方听的很不耐烦,只要他们签名增加曝光率,有些多嘴了,诱惑力很大,没得商量,很固执,谈崩了。
可见,这一解说形式是博主对电影某一情节点的概括、筛选并剪辑,在保留原影视作品视听语言基础上,采用字幕形式概括画面内容,或描述电影情节走向,以提升短视频用户对影视情节的认知效率,在此过程中影视情节信息得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有效传播,而影视作品本身的视听艺术性则被大大消解。
(二)内视角:影视人物命运的情感聚焦
内视角即第一人称视角,在影视解说类短视频表现为影视人物作为叙述者解说影视剧的类型。内视角是影视剧中事件的观察者与参与者,其与影视剧中其他人物之间存在各种关系,在此类短视频中呈现为人物独白式解说文本配以相对应的影视片段。通常来看,此类影视解说短视频通常不像外视角叙述一样站在上帝视角开展影视解说,而是多从剧中人物视角的“心理独白”展开叙述,因而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与感情色彩。正如申丹所言,“人物——叙述者的在场‘可能会用前景化的情态’加以凸显,‘强调其判断和看法’”[8]。不难发现内视角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叙事形式为“影视作品情节点+影视片段+人物独白解说词”,例如,自媒体博主“小易搞笑解说”解说电视剧《狂飙》时,短视频开端为高启强与泰叔争夺集团权力镜头画面,将短视频用户引入影视情节点的叙事情境,继而展开解说:
我是高启强,本是菜市场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鱼贩,在那超市腥臭的鱼摊前忙碌,只为能多挣几个辛苦钱养活弟弟妹妹,我起早贪黑守着鱼摊,双手泡在冰水里冻的又红又肿,可即便这样生活的重压仍让人喘不过气……
此类短视频在视频开端插入原影视作品中的主线情节点,如果将次要人物作为解说者,则会选择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的矛盾情节点,将之作为短视频开头建构起影视情境,从而引出次要人物内视角叙述者的心理独白,并采用其人物配音进行回顾影视情节的解说。
通常来看,外视角叙述的影视解说方式,口语化解说文本是此类短视频的主要输出内容,解说文本重在阐述情节,以叙述者视角口语化形式为影视作品进行解说配音,影视作品的叙事逻辑在短视频中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自媒体博主对影视作品主观化的情节重构。相较于外视角的影视解说,内视角的叙述是自媒体博主基于影视剧中人物视角所开展的固定视角叙述。在由外部视角向内部视角转化的解读过程中,解说文本由侧重情节描述转为回忆性独白,解说词叙事性会大打折扣,很难呈现出影视情节原貌。但是,作为内视角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具有鲜明的独白特性,能够使得短视频用户从特定视角实现对该影视剧中次要人物对外部世界、人物关系的内在感知,并阐明人物行动的动机。同时,由于短视频篇幅短,外视角影视解说类短视频难以覆盖整部影视作品的情节线,基本从主情节线进行介绍。而对于诸多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黏性用户来说,对于一部他们没有观赏过的影视作品,内视角影视解说类短视频以某一角色内视角讲解一部影视作品的形式,显然是一种对影视人物形象与情节的有益补充。这种从影视剧主要人物、次要人物等不同视角的解说,有助于短视频用户建构起对影视剧人物形象、人物性格的认识,更易使短视频用户了解影视人物内心活动,在了解人物矛盾关系、行为动机的基础上产生审美移情。
三、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技术乱象
数智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短视频创作与生产。在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创作过程中,AIGC也被全面应用至解说文本写作、克隆影视角色解说声音音色等各方面,在为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生产提供技术支撑的基础上,它极大推动此类短视频解说形式的多元化发展,最具显著性的即叙述视角的转变。与此同时,AIGC赋能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用户创作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表现为质量与数量不匹配、人文思辨不足等弊端。
(一)AIGC赋能,影视媒介的秩序重组
AIGC与短视频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短视频类型及其创作形式的多元化发展。从创作端来看,对于想跻身影视解说类短视频自媒体博主来说,创作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影视鉴赏、影视剪辑、影视解说文本、影视解说配音等创作能力要求较高,而生成式人工智能运行技术的大众化应用,体现在影视解说文本、语音技术模型工具的不断涌现,基于深度学习算法,这些AI模型能够根据自媒体博主用户指令筛选海量案例,确保快速生成一篇影视解说类短视频文本,继而依据用户文字内容进一步选取相对应的影视片段进行剪辑与拼接,并可以选择音频、视频剪辑软件的不同音色模板进行配音,从而完成一条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制作。而影视解说类自媒体博主只需要对于AI生成的内容进行检查与调整,即可有效率地生产与传播。
另外,2024年以来,伴随着AI语音合成技术的成熟,促使许多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博主能动地使用AI技术,以提升此类短视频叙述形式的表现力,即“声音复刻”技术赋能内视角影视解说类短视频,表现为解说视角由“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转变。在此生产过程中,AI模型能够从短时间音频中捕捉并提取语音中的基础元素,从而快速搭建起一个声音建模框架。就大量内视角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解说音频来看,不仅能准确复刻人物音色或发音特征,甚至能够还原影视剧中角色的口癖、停顿、发声方式等讲话习惯。由此可见,使用影视作品演员声音开展解说的短视频音频动态性表现已十分流畅,AI语音合成技术帮助影视解说自媒体博主从“真人语音口语传播”环节解脱出来。无可否认,影视解说类短视频作为一种影视快餐,已经成为大众最常见的影视欣赏方式。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无法达成人类对影视艺术的感知力,因此尽管短视频用户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生产,大大提升了生产与传播效率,以补充短视频市场极高的观看诉求,但是却无法保证影视解说内容的准确性、独创性。
(二)过度量产,质量把关需提升人文思辨
当下全媒体语境下的影视生态已经发生改变,影视解说类短视频作为一个影视传播的重要场域,并以一种碎片化的影视信息渗透至大众日常的影视鉴赏活动之中,新媒体观影成为大众有效了解电影、电视剧等大众文艺的首要渠道。显而易见,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对于大众视听文艺起到反向影响与宣传效果,诸多短视频用户在未观赏影视原作品的背景下,其对于该影视作品的认知就来自于影视解说类短视频。
此外,基于算法模型对短视频用户的推荐,搭建起短视频用户对于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观看习惯,短视频用户在以往观看一部电影、一集电视剧的时间内,通过自媒体博主的解说,实现对几十部影视剧解说短视频信息的获取。这一种观看方式的变化,显示出互联网时代,大众对于信息接受速度与效率的要求不断提升,甚至是放纵式观看的影视审美现状。面对短视频时长短,观看速度快的传播特性,影视解说类短视频数量需求大,而鉴于影视解说类短视频AI技术的下沉,其内容生产趋向模板化,大量的短视频新账号仍然以吸粉丝、追流量为内容生产导向,而这种AI工厂快速生产的影视解说,既没有创作者作为把关人对短视频进行文艺审美把关,短视频平台作为传播渠道也难以对大批量影视解说视频的内容质量把关。可见,数智时代的影视解说活动理应强化创作端的把关建设,尤其是影视解说类短视频自媒体博主自身媒介素养、文艺理论素养的建设,以往的影视解说博主大多为具有影视文艺批评素养的自媒体博主,其解说活动是建立在丰富阅片量与高水准影视审美感知经验基础之上。而伴随着AI技术的发展,一条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在用户的指令修改中就能够快速生产出来,而此类短视频也广泛存在字幕错别字、情节描述错误等问题。因此,在影视解说类短视频井喷式生产与传播的背后,我们很难不对短视频博主对原影视作品的感受力与阐释力打一个问号。在短视频平台作为大众最活跃的信息娱乐场域的背景下,在AIGC生产的影视解说内容充斥在新媒体语境中,影视与短视频之间的生态关系恐很难维持,显然也不利于培养短视频用户作为影视鉴赏主体的审美思维。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视域下,美国传播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E.M.Rogers)提出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s),其认为创新经过一段时间经由特定的渠道,在某一社会团体成员中的传播过程中的不同接收程度。罗杰斯按照社会中接受新鲜事物程度进行人群划分为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多数、晚期大多数、滞后者。通常来说,创新者往往是具有较好教育素养的人群,并具有较多的媒介接触行为。以往网络影视解说类视频是由一个团队进行的专业化生产,往往具有较为深入的影视批评观点,并形成了一定的解说风格。而在生成式AI的介入以来,影视解说类短视频自媒体的专业性与文艺批评特性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发现了此类短视频是成本低、易吸纳粉丝类型的博主所进行的盲目生产,而影视解说也带有浓厚的、大规模复制的“AI味”,显然,自媒体博主作为第一道“把关人”的责任缺失。也正因此,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内容的生产与把关问题亟须重视。
目前来看,影视解说类短视频选择的影视文本倾向于中外影视经典作品,伴随而来的是影视二创的同质化、解说影视作品的重复化等问题。因此,基于AIGC语音合成技术的成熟,促使转换叙述视角的“独白”式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大量涌现,并为此类短视频创作注入新的活力。但是,伴随着借助AIGC所生成的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对影视作品的二创停留在对影视艺术的消解层面,面对当下影视解说类短视频对大众影视欣赏方式的普及,其对影视艺术的反向影响是显著存在的。因此,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流量导向需要建立在一定社会价值导向的基础上,经过博主人文思辨的创作,而非淹没在浅薄化、AI味、网络话语中的娱乐至死导向中,影视解说类短视频需要肩负起普及影视艺术、宣传影视艺术的任务,这一点还需从创作端寻求出路。
[1] 张一玮《声音与现代性:默片至有声片过渡时期的中国影院声音史问题》,《文艺研究》2010年第5期。
[2] 张伟、严洁琼《默片时代的“配音”与“配乐”》,《电影新作》2010年第2期。
[3] 约瑟夫·安德森、孟静慈《日本的有声默片:活弁及其语境》,《艺术评论》2010年第3期。
[4][5]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第254页。
[6][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钰、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7] 申丹《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7页。
[8] 申丹《跨学科视野下对Point of View的重新界定》,《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