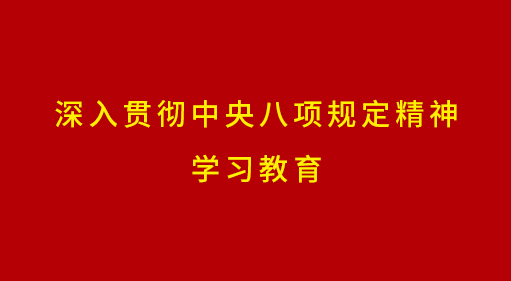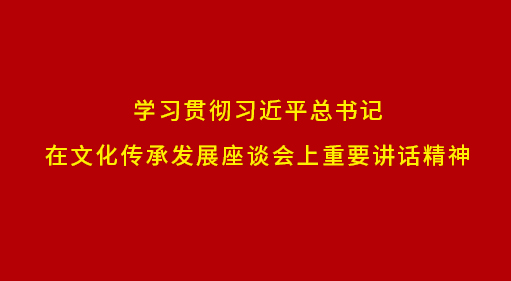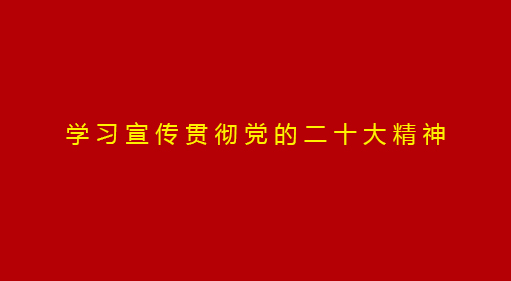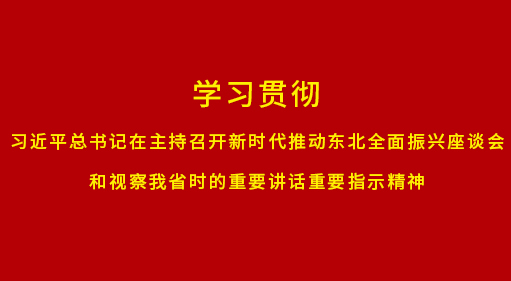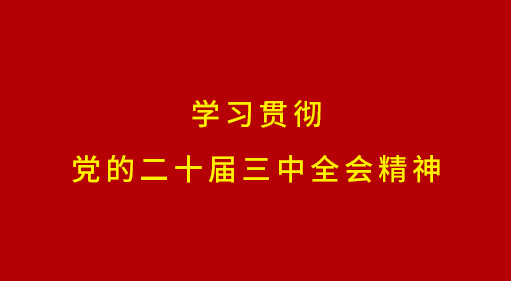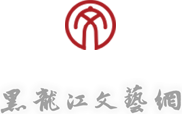诗意的重新确认与想象的跨媒介新变——思考21世纪诗歌的一个视角
时间:2025-07-22
鄢 冬
摘 要: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诗意这一观念有着特殊的价值指向,对诗意的理解也存在着相呼应、相碰撞等不同状态。进入21世纪以后,诗意泛化成为国人日常生活中较为瞩目的文化现象,这一定程度归因于以诗歌为代表的诗意载体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一些令人关注的变化。以21世纪诗歌及近年来诗歌跨媒介传播事件为范本,不仅有助于重新思考诗意的当下症候,也能够反复探寻诗与诗意的未来指向。诗人独特的诗意想象如何实现技术转向并真正参与到日常生活的诗意泛化行动中,值得深思并探讨。
关键词:诗意;跨媒介新变;21世纪诗歌
引 言
当前诗人的写作环境被各种新兴媒介技术围困。新媒介是时下学界探究的热点,也是大众生活中无法避及的焦点。与20世纪媒介技术不同的是,21世纪的新媒介技术更彻底地依托于网络传播技术,它的更新速度之快越来越超乎想象。如果说之前的新媒介技术只是作用于诗的传播和接受,那么随着微软小冰、Kimi、DeepSeek等智能程序的出现,诗的生成也不再神秘,寻常百姓都有写诗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在各类网络舆论中,读者仍然自发地为“诗”正名,总是掀起“诗是什么”的讨论。回顾以“梨花体”“羊羔体”“白云体”以及贾浅浅事件为代表的种种争论可知,尽管21世纪新诗的外在形式和表达内容固然有技术“赋魅”的成分,但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在诗中寻找“别趣”的诗意却仍然没有改变:比如,据有关人士统计,有60万人在快手写诗[1],“外卖诗人”王计兵登上2025年央视春晚,而地铁站、广告牌、广场、公园的“诗之语”更是屡见不鲜。“诗意”去哪儿了?“诗意”如何走向未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前,首先要确认当下的诗意内涵以及思考想象与诗意如何同构发生。
一、对“诗意”的当下确认
诗意的准确内涵究竟是什么,自古至今难有定论。王家新认为:“‘诗意’,这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更新的命题。”[2]荣光启认为,关于诗意的确认关乎新诗的合法性:“当代新诗有多重分裂。首先是读者对新诗的不信任,认为新诗无‘诗意’。”但他认为,诗意不应是一个预设的概念,它应该兼具时代性和经典性,不能被“刻舟求剑”式对待:“‘诗意’不是先在的,而是生成的,与语言、文化环境相关。读者以对待旧诗的‘阅读程式’来‘归化’新诗,故看不到新诗的‘诗意’。”[3]
从古代延续而来的“诗意”总是具有强大的消化能力,它将“诗之本质”“诗之意义”“诗之韵味”等多种内涵都悄悄吸收。一些学者或诗人们在思考“诗意”时,都将其视为一个预设的先在条件,或是“应有之义”。总体而言,古代诗论所说的“诗意”主要围绕诗歌文本,进而对文本中的诗性语言、诗味氛围和诗韵意涵等内容的概括性总结。然而,在浩如烟海的诗意论断中,其实直接出现“诗意”这一概念却并不多见。
刘禹锡的《鱼复江中》出现了“诗意”字样。分析这首诗可以发现,诗歌中的“诗意”一方面发乎于山水之间,另一方面也是自身理想的一种寄托[4]。同时,唐代诗人朱庆馀的《送吴秀才之山西》也出现了“诗意”。对比两首诗,有一个共识性的现象:“诗意”的出现都与自然山水有关。但是,刘诗中“客情浩荡逢乡语,诗意留连重物华”的“客情”实则反映着窘困的贬谪之旅,继而“诗意”成为一种精神质素并投射出诗人的乐观旷达的生存态度。在“乡语”与“物华”中滋生的诗意让诗人将他乡认作故乡,“苦中作乐”也有了更为切近的现实理由。
由于中国古代文论重兴发、感悟,轻体系建设,因此中国古典文论中的“诗意”论也少有系统论述“诗意”的概念发生及流变。同时,研究者几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诗意泛化为诗的本质意义:“诗意学说是中国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5]比如,以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为代表的宋代诗话被认为是诗意理论的集大成者:“总之,宋代诗话对诗意理论进行了较系统的表述和建构,这有机地体现在诗歌审美本质论、诗意特征论、诗意创造论三个相互联系的动态系统中。”[6]在《岁寒堂诗话》中,张戒将杜甫诗作与王安石等人诗作进行对比,进而认为,杜诗才是真正的诗,以其“吟多意有余”“诗尽人间兴”[7]为代表。实际上,以相对严谨的标尺衡量,张戒书中所提“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8],显然带有理想主义的浪漫想象,不具备实际的阐释意义。但随着以宋代诗话为代表的“诗意”论对“意”无限拔高的同时,“诗意”也慢慢脱离了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在天下体系崩塌,世界感剧变的近现代中国,这一完整的诗意系统,词与物之间形成的精致结构,也注定成了一种俗套的,渐渐与中国人的经验和心灵严重疏离的语言和诗意的牢笼。”[9]
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古典意义上的“诗意”已经难以与人的生存产生自洽了。对于古人而言,自然山水就是人类社会的另一个镜像,在山水中感受或表达诗意,成为古代诗人的常态。诗人在山水中寻找到的诗意无疑弥补了他们灵魂中的缺失感。“西方诗歌传统自古希腊起就有诗神缪斯。诗的灵感的人格化身的神话,诗以其灵感通天地,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人生哲学”[10]。然而,工业文明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对话关系,让人的主体地位尖锐地突出,而这时的艺术作品尽管仍然对自然与人的关系有所思考、有所表现,但是“自然”由人的“诗意栖居地”已经慢慢演变成精神的乌托邦,进而“诗意”不再是连接自然与人的情感中介,它慢慢转移为停留在人的艺术体验中的诗意创造:“写作就是把反诗意的世界,纳入诗意创造中;在诗与非诗的对立之间,找到合适词语熔接点;把词与物之间对立,化解为诗意的无阻碍的赞颂。”[11]
无论是诗人刘禹锡一脉表现出以自然为友、安贫乐道的“诗意”之乐,还是以欧阳修、张戒、严羽、司空图等为代表的“以意为诗”体系,恐怕都难以解释21世纪新诗文本中被诗意泛化的日常生活。对于21世纪诗歌而言,诗意的认知困境在于:读者更多时候所接受的是古典范畴的诗意,而诗人却不得不以更为现代性、更具技术特征的方式表达诗意,但诗人的这种表达方式有时还未必能够获得学界的肯定:“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诗人歌声的时代吗?先锋派和实验派的文学固然揭示了谎言,但它自身大多是欲望的鼓吹和技巧的玩弄。”[12]
之所以读者关于“诗意”的认知导向了古典范畴,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国民教育中较为悠久的古典诗词内容。“从小学到中学,古代诗歌的选取已有相当的比例了,目前比较欠缺的是新诗教育”[13]。新诗教育被“应试”指令所排斥:“而在实际的新诗教学现场,较为普遍的现象是:要么‘应试’指令压抑甚至排挤了课堂教学中的新诗教学内容,要么教师和学生面对新诗教学产生了‘畏难’情绪。如此久而久之,新诗教学乃至教育在实践中逐渐变成了一个难题。”[14]新诗教育的缺失,使大众对诗意的认识缺乏一定的时代性:“如何让群众重新找到对中国的现当代诗歌的审美感觉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育问题。”[15]曾经因“梨花体”事件备受争议的诗人赵丽华在谈及另一舆论事件时也这样说:“但是受教科书影响的这一批读者,他会认为诗歌必须是什么样的,必须有自己的格式,必须诗言志,必须是有承担的、有负载的、有一些正能量的……但如果大家要看多了罗伯特·勃莱的诗,看多了布劳提根的诗,看多了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诗,看多了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诗,心中有一个大的创作的自由,那无论看到什么样的诗,就都不足为怪,就会允许在诗歌上做各种的探索。”[16]
认知当下诗人的“诗意”书写,首先需要更清醒地认知他们的表达方式。以AR、VR为代表的XR(Extended Reality)技术日益兴盛,让诗情画意已经不必通过亲身体验(或书写)来表现,而是通过“诗意镜像”的方式让受众沉浸其中。尽管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依然焕发着生机,但也都无一例外地依赖于新的技术手段呈现。在这种前提之下,当下新诗书写中有哪些新的诗意质素进而获得读者和批评家的重新关注,成为诗意确认的关键问题。
二、智性书写:诗意与想象共同体的特殊勾连
就当下语境而言,诗意可以从两条相对清晰的脉络建立意义体系:一是仍然从诗出发。新诗与古诗语境中的诗意表达并不相同。新诗诗人并不热衷制造一种诗意的氛围或情境,而是更多通过语言的智性、象征隐喻的陌生化来表达诗意。因此,此处的诗意更多是一种诗之秘意的体现。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属于新诗的诗意表达就越发独立且清晰了。诗人总是以一种内省的态度,向日常生活或向公共生活挖掘具体可感的诗意。同时,跨媒介的艺术交往行为,不仅让“诗意”的传播更为便捷,也让各艺术门类的诗意通过不断交叉互融的方式最终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另一类情况是,“诗意”已经长期被泛化使用在各个领域,它不仅仅只表达一种审美状态,也可以指涉行为方式的具体内涵,尤其可能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被频繁进行符号性的传播。诗意往往促成了想象共同体的生成,进而逼迫我们追认一个民族的潜意识:“一个民族永远无法跳出他自己的潜意识、无意识中无声的语言,而生存、而认识世界。”[17]每个民族认识世界时,势必带着自身的局域性、族别意识,但是,诗意却有机会成为不同民族共通的思维质素:“实际上,它的意思不过是,这个现实的世界的本质应该是诗意的,应该具有审美性质;这个世界的意义应该是诗一般的充满柔情,应该有想象的地盘,有审美的感觉。”归根结底,“诗意的世界”即是将客体世界主体化,将活动主体诗意化:“现实生活世界的中心是人,生活着的人,诗意化的世界,实质上应是诗意化的人;人的诗意化,世界才能最终审美化。”[18]
进一步论之,如果把生活中的诗意看作是诗意的“外溢”,那么当下新诗对语言智性的追求则是诗意的“内收”。对于当今诗人而言,需要对抗的就是制造语言陌生化的焦虑,而诗意也主要由此产生:“这种‘空白’感作为一种与现代汉语诗人共同诞生的焦虑,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被命名和说出……由于这种孤独的处境,促使现代汉语诗人不断创造词语的暗示结构,以新的方式伸展出言外之意。”[19]相比于古诗,新诗的诗意没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消极避世、积极隐退、独立人格等);相对于20世纪新诗,当下诗歌“抒情性”则愈加缺失。
在诗意的“外溢”和“内收”之间,人面对自然的灵魂豁免正在消失。在泛诗化的日常中,更应强调人如何在社会中“诗意栖居”,如何向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自然和宇宙)散发人文精神。与此同时,作为诗歌中的自然书写也发生着肉眼可见的变化。直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或讴歌,已经不是诗人所热衷的情感脉络。比如,南欧的诗《牵一匹马回家》[20]不再以讴歌者或仰慕者的姿态书写草原,也没有将马作为一个凝聚性的中心意象,而是贡献了诸多惊艳的语言片段,如“我把它牵到城市,它仿佛/被选择。但我听到时间断裂的声音/从它背上掉落,就像那些/很古老的碎片”。“马”不再当作一个惯常的意象,但依旧流畅地、有节奏地被诗的叙事逻辑处理,从“时间断裂”的“古老的碎片”生发出陌生化的语词之意都围绕“马”进行。相佐证的还有柏明文的《焰火》等诗作,柏明文在形容焰火时,称其为“时间之灰”,颇抽象且陌生化[21]。21世纪诗歌文本中还经常出现“孤独”“死亡”“记忆”“生活”等相对晦涩的词汇,而并非像既往的诗歌经验那样,必须借助日常化的喻体来表现。如果说,古代诗歌更多以意境衬托意象,20世纪诗歌更多以意象串联意境,那么21世纪诗歌的书写经验则是以文字为诗意的起点,用更抽象化的张力展示一种野蛮、自由的生长状态。对于21世纪诗歌而言,一花一叶、一句一词都能展示出诗意的轻巧感、狡黠感。诗意不再于具体的情境相联系,场景的言说演变为细节的言说。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则是想象方式或范型的变化。想象首先是基于形象的概括:“以上表明,想象的概括,就是形象的概括;想象的过程,也就是用形象思考的过程;想象的结果,也只有用形象来体现。所以我们说,想象就是一种用形象思考的思想方式。”[22]记忆为诗人提供物质素材,而想象则体现出创造性的建构,联通奥妙的精神秘境。高扬的想象力让惯常之境滋生出诗意。但此处的想象绝非幻想,而是诗人或艺术家独具匠心的创造性想象:“这种想象力不只是起联想的作用,而且具有建构的能力(constitutive)……这种‘本身不出场的出场’就是具有建构性的、创造性想象。”[23]在这种典型的想象范式基础上,才产生出艺术的真实:“想象创造真实,文学和艺术是想象的产物,因此文学和艺术具有真实性,浪漫主义批评家们以回到柏拉图的方式重新解读了亚里士多德的诗的‘哲学意味’。”[24]
诗人首先是生活的“在场者”,但想象的一个重要属性即是“飞离在场”:“想象,不管在哲学史上、心理学史上、美学史上有各式各样的界定,但都有飞离在场的意思。”[25]21世纪诗歌实践表明,诗人的想象范型是既“在场”又“离场”的存在,但更偏向于“在场”感,是一种“合理化”的想象,而非“超拔”的、“飘逸”的想象。在21世纪诗歌中,物象往往不容易转变为意象,抽象的象征性语言被更为精密的细节书写取代。比如,在王学芯的《看云》一诗中,除了首句“云造出一座山”以外,没有再出现“云”字。如果是古代诗人写云,要么将云寄予某种理想,如王维《终南别业》中的“坐看云起时”;要么将云视作烘托意境的典型意象,如杜甫《春夜喜雨》中的“野径云俱黑”。即便在20世纪诗歌中,以“云”为代表的物象仍然有机会成为抽象化的意象符号,比如顾城的《远和近》中,由于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诗人又将“远”和“近”这一组空间概念附着在形象之上,因此两组辩证法让“云”符号化、意象化。但是,在《看云》[26]这首诗中,诗人更迷恋于通过细节、事件的铺陈和讲述来呈现云的日常之态以及与人的关联。读者企图从诗人惯常的意象制造、修辞运作中窥探想象力的高深,看起来已经不那么现实。但是,诗人的想象力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内遁于文字之中。诗意不再来源于诸多超验性的想象,即便这曾经是诗意世界的组成要素:“从超验的原则来设定世界,可以说,就是诗意化世界的核心。”[27]
个体的想象力与个人气质、天赋、经历有关联,集体的想象力则需要从集体记忆、民族心理等角度探究。同样,当21世纪诗人由外向性的想象力创造转变为一种“内敛”式的呈现方式时,对文本中“象”的创造慢慢转移为对语象的烘托。智性书写,就成为搭建21世纪诗歌想象共同体的特殊方式。归根结底,文字植根于人类生活,自然而然无法完全脱离其所指世界。但与此同时,当意境的制造不再是诗及其他艺术形式的专属,那么至少“遣词造句”依然能够表达诗意,因此,诗意也日趋日常交际化、口语化以及实用化。
三、诗意想象的跨媒介新变
准确地说,诗意与想象这两个概念与诗人有关,DeepSeek让人人都可以写诗,但其使用者不能称其为诗人。无论是诗意或是想象,都不是使用者主动创造的,而是算法数据化的产物。其实在这些写诗程序出现之前,21世纪诗歌就以跨媒介的形式出现在各个领域。借助媒介技术,诗人心灵呈现世界的“管窥”式想象发展为“朗照”式想象:“由此看来,美不是理念的显现,也不是对实在的模仿,而是人的审美判断力即审美想象力对诗意生存之境的开启和朗照。”[28]与此同时,这种朗照的方式并不是一览无遗式的,而恰恰是以诗意为起点的:“广义的诗意和精神的完整、和谐、充实、圆满的体验相关,是人在生命存在中所能感受到的一种特别的精神性韵味。”[29]
智性书写与想象勾连,形成诗意现场,而跨媒介传播方式又让21世纪新诗频频破圈成为舆论焦点。在被网络舆论发酵的新诗事件中,围绕诗人身份的合法性、诗中的伦理观是否妥帖、审丑表达是否恰切等问题形成了热点、爆点。综合这些事件的批评声音,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责赵丽华、车延高、乌青、贾浅浅等人的诗歌写作过于口水化,如唐小林的言论极具情绪性:“贾浅浅的诗歌完全属于一种‘回车键分行写作’。这种白开水似的‘浅浅体’诗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无聊当有趣,把废话分成行——仿佛是一路狂按回车键的产物。”[30] 类似的观点也同样出现在对“梨花体”“羊羔体”“白云体”的评论中;另一类则是聚焦于新诗诗人的题材选择是否失之偏颇,如贾浅浅的诗由于包含了不雅的物象而被称为“屎尿诗”。同时,贾浅浅的副教授(名作家的女儿)身份、车延高的公务员身份又给公众增加了若干加码揣测的空间。
对于这些事件的认知有时并不一致。有学者评价贾浅浅的诗是诗意的:“诗人是在世界的暗夜中呼唤圣灵的人,那么诗人贾浅浅首先唤醒自己内在的诗意,使得澄明在语词之中闪烁。”[31] 两极分化的认知态度还是源于对诗意的不同判断。如前所述,21世纪诗歌的诗意表达主要体现为对语言智性的挖掘上,这反而进一步地解放了诗人的艺术想象力:诗人通过合适的文字表达对世界的诗意认识即可,不需要通过较为复杂的诗意技法再现出一个完整的平行世界了。诗意的存在变得具体且可感:“诗意的存在是被美好感浸润的存在,是澄明的存在,而不是空虚的存在,不是无意义的存在,不是异化的存在,不是被物质欲望与社会奴役的存在,不是动物式的存在。”[32]因此,这一理论接近于当代诗话哲学的内质:“说到底,诗意化的世界就是这样设定的:超验的大我通过一个禀有感性的小我,把有限之物、时间中的物(包括个体的人和世界中的事物)统一领入无限中去。”[33]
新的媒介环境树立了碎片化、易变性的认知图景,使得诗人不太可能从容生成典型化的想象范型,诗人往往通过较为生活化的想象重组语言材料。换言之,当下关于诗意的想象即是多元的、灵活的,但又是贴近于象的“物性”因此也显得更具生活质感。因此,关于诗意的认识也应该多元化。已经有学者对古典主义时期和现代社会的诗意表达进行区分。哈弗洛克这样认为:“但如果我们考虑诗歌的功能完全变了,文化情景完全变了,那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柏拉图论述诗歌时,他说的那种诗歌真的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诗歌。”[34]同时,他认为,诗意实际上是可以在一个纯技术的层面上实现的:“这是真相(与欺骗相对),缪斯们借以掌握知识的真相。这绝不是与散文和说明文相对的诗歌的真相。相反,用现代非功能的意义,这里的真相应该相当于‘诗意的’(poetic)真相。那就是吟游诗人采用的骗人的吟唱:叙事的虚构、情节、戏剧和人物。”[35] 王家新也有类似的看法:“总之,我们已很难用传统的趣味和标准来描述中国现当代诗歌‘诗意’的生成机制’了。要进入到这种内在机制之中,我们几乎需要重新发明一套精神的和诗学的语言。”[36] 这背后的逻辑在于,如果依旧停留在古典诗学的层面看诗意,实际上它存在着被高度政治化的倾向:“总之,如果我们用柏拉图的诗歌观念来看前文字时代的情况,这个观点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彼时,古典时代的希腊制度刚以其特有的形式结晶成形。诗歌不是‘文学’,而是政治和社会之必需。”[37]
当各种媒介技术通过虚拟成像的方式部分代偿了包括诗所能给受众提供的想象空间,诗意将慢慢回归为一个形式问题:当诗语言本身的小众性和精英化叙事难以满足受众对诗意大众化的期待时,语言的能指形式该做何种改革?近年来,新诗文本的口语化、段子化让诗被争议、被边缘化,但也获得了一定的大众性,若干诗意的表达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渗入日常生活。也就是说,当诗人想象更纯粹性地通过文字表达而非借助隐喻、象征等技巧时,文字成为真正的“存在之家”。诗人既要追求自身的艺术独创性,也要试图消弭“歧义”:“不过,诗人也应意识到,超现实的诗性想象力为文本增添了独特的质感,但也可能催发歧义,使读者无从破译诗歌的密码,导致阅读的滞涩和思维的中断,因而还应注意维护‘经验’与‘超验’的平衡,使读者和文本间的沟通渠道更为畅通。”[38]如果以这个视角来看待贾浅浅诗歌中的诗意,可能就颇具玩味了:在贾浅浅的诗中,一些不适宜入诗的意象无疑刺伤了读者对古典化“诗意”的追求。但是,运用反常的语词的确产生了陌生之“诗意”。
在当前与诗有关的各种跨媒介交往行为中,尽管文字媒介的中心地位也受到了挑战。但是,文字所给予受众“回甘”式的想象仍然没有中断。一方面,文字仍然需要负载有效信息,还需要传递着信息发送者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诗本就是语言算法的“游戏”。诗人在超越了语义的表象层之后,超拔的想象以及它所促成更为多义的精神世界仍然有机会与读者产生深层次的共融。同时,从一个更为宽阔的视角观察,诗不仅产生了不同的诗意表达,其诗意想象还有机会通过传播媒介在不同的艺术轨道上再次传递。这时,诗意就可能不再只以智性创造的方式存在,而是形成一个具有辐射性的“诗意中心”,进而影响着日常生活的审美世界。
结 语
新媒介语境并非只是给诗人单纯提供一种技术背景或是实验性的空间,而是以复杂、多变的媒介技术向内刺激诗人的感知屏障,进而产生更开放的意象体系,同时一定程度地裹挟着诗人冲破固有圈层的壁垒,从而实现诗意的“泛化”。“想象”的确不再是一个具有精英立场的专有术语,它可能由各类更为便捷的技术手段“代偿”实现。但是,只要人类围绕于文字的交流或争论不会停止,诗人在智性书写之上所展示的想象力仍旧具有文化意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诗意”正通过更具普泛性的想象力走向未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世纪中国古代诗词跨媒介传播现象研究”(项目编号:2024BZW021)阶段性成果]
[1] 单读《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351页。
[2][36]王家新《从古典的诗意到现代的诗性——试论中国新诗的“诗意”生成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5期。
[3] 荣光启《“诗意”上的分歧:当代新诗的读者与作者》,《华中学术》2020年3期。
[4] 按照孙丽编著的《刘禹锡全集》(崇文书局,2018年版,第330页)所注,本诗作于824年,正是刘禹锡离开夔州到和州的途中所作。
[5] 张思齐《张戒的诗意学说》,《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6] 胡建次《宋代诗话中的诗意论》,《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4期。
[7][8]陈应鸾《岁寒堂诗话校笺》,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04页。
[9][19]颜炼军《象征的漂移:汉语新诗的诗意变形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0页,第94页。
[10][17]郑敏《新诗与传统》,北京:文津出版社,2020年版,第10页,第115页。
[11]颜炼军《化解对立面——试谈当代汉语新诗中的矛盾修辞》,张曙光、萧开愚、臧棣主编《诗意的重新命名》,《中国诗歌评论》2012年秋冬号。
[12]彭富春《文学:诗意语言》,《哲学研究》2000年第7期。
[13]徐芳《百年新诗传统、诗歌教育与其他——吴思敬教授访谈录》,《文艺论坛》2023年第1期。
[14]张桃洲《新诗教育的困境及可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15]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16]韩忠林、杨雪情《16年前被传为“黄瓜诗”作者的赵丽华:当时想把全世界的电脑砸烂》,《河南商报》2022年9月7日,第A09版。
[18][27][33]刘小枫《诗化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第46页,第53页。
[20]南欧《牵一匹马回家》,中国作协创研部《2014年中国诗歌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页。
[21]李敬泽、张清华编选《中国诗歌年选》,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22]李传龙《论想象》,《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23][25]张世英《论想象》,《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24]张冰《论想象:从哲学到艺术》,《文学评论》2021年第6期。
[26]张学芯《过来过去》(组诗),《当代•诗歌》2024年第2期。
[28]谭容培、颜翔林:《想象:诗性之思和诗意生存》,《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29][32]丁来先《诗意人类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第81页。
[30]唐小林《贾浅浅爆红,凸显诗坛乱象》,《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1期。
[31]朱必圣《澄明的诗意——浅议贾浅浅诗集〈椰子里的内陆湖〉中的诗歌》,《文艺争鸣》2020年第8期。
[34][35][37]哈弗洛克《柏拉图导论》,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年版,第27页,第70页,第84页。
[38]卢桢《新世纪诗歌的写作精神与想象空间》,《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2期。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