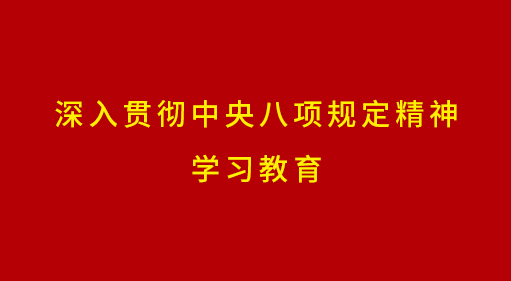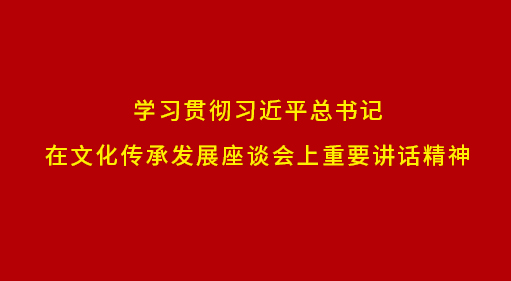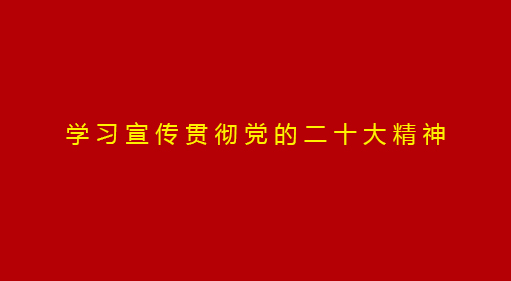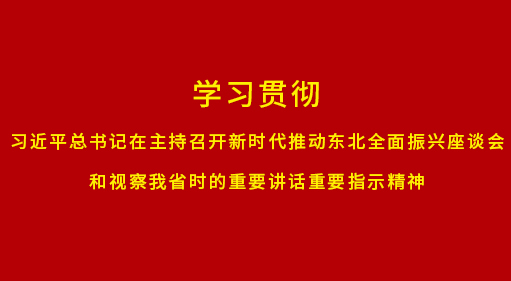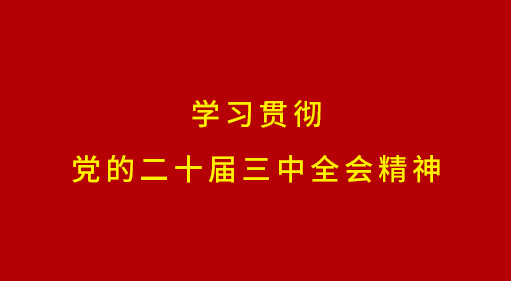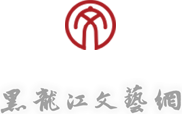童年经验・文化坚守・生命哲思——迟子建追忆散文的三重内涵
时间:2025-10-31
周晓燕 金铭霞
摘 要:迟子建的追忆散文极具温度与深度,《灯祭》《故乡的吃食》《蚊烟中的往事》《农具的眼睛》《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散文以黑土地为精神根系,或回溯童年岁月,或描摹地域风情,或探寻生命本质,既展现出东北乡土的独特风貌,又蕴含着对人性、文化与生命的深刻思考,构成了其文学世界中鲜活且厚重的散文图景。剖析童年经验、文化坚守和生命哲思这三重内涵,既能洞察童年、经历、时代对个体情感记忆的塑造与影响,又可精准把握迟子建创作风格的蜕变路径与内在文学思想体系。这种传承与创新为中国当代散文发展注入了独特活力。
关键词:迟子建;追忆散文;童年经验;地域文化;生命哲思
黑土地为迟子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叙事素材与精神滋养:这里承载着道不尽的童年记忆、摹不完的乡土图景与咏不绝的生命颂歌。在追忆性散文创作中,作家广泛运用时空叙事策略、主观指向性表达及极性程度句式,通过聚焦生命历程中的关键节点与核心感悟,实现了对个体生命经验的提炼与重构。具体而言,童年生活回溯精准呈现了民众日常生活本真,故乡变迁慨叹凝结着对民族与地域文化的守护意识,生命本质洞察则折射出对历史文化命题的深层思考与理性观照。
一、童年经验:心灵原乡的深情镌刻
迟子建以细腻笔触深情回溯往昔,将家庭生活中的亲情滋养、个性培育与艺术启蒙,转化为文学创作的丰沛素材与精神内核。家庭不仅为她提供了情感的栖息之所,更通过宽松的成长环境、无声的艺术熏陶,在其内心深处镌刻下独特的生命印记。这些童年记忆不仅成为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与主题,更构建起其观照世界、书写生命的独特视角。
(一)童年际遇与原乡建构
家庭环境所涵盖的教养方式、情感互动模式及培养取向,不仅对个体成长具有终身性影响,更在作家文化心理结构的生成与艺术个性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父亲在迟子建的童年记忆中扮演着精神启蒙者的角色。无论是《故乡的吃食》中牙痛时被父亲抱起共赏月色的温情时刻,还是《灯祭》中父亲以废旧罐头瓶精心制作节日灯盏的仪式化行为,均展现出父性力量对儿童审美认知与生活信念的培育。这种情感传递,不仅构筑了童年的幸福记忆,更在其心灵深处播撒下对生活诗意感知的种子。母亲则以坚韧不拔的生命姿态,成为迟子建精神品格的重要参照,《奏捷之驿》中母亲年轻时携子返乡的执着,不知不觉内化为女儿的归乡情结,如《灯祭》中所说,不管身在何处,她总是要回家过年。在《会唱歌的火炉》中,与姐弟一起伐树锯木、共享“美食”等童年往事,构成了多维的感官记忆网络,这些浸润着泥土芬芳与亲情温度的生活场景,彰显出家庭记忆对个体生命轨迹的深远影响。
在认知世界、锤炼品格与建构价值观的童年与少年时期,北极村以其鲜明的风土人情、瑰丽的自然景观及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形态,深刻塑造着作家的创作基因与艺术风格。在迟子建的记忆图谱中,家庭之外的邻里、师长与同伴群体同样不可或缺。《哑巴与春天》中命运坎坷的哑巴、《中篇的江河》中的苏联老奶奶、《水银花开的夜晚》中严厉的赵老师、《论谦卑》中精神失常的男同学等人物群像,共同构建起充满烟火气的乡土社会图景。童庆炳指出:“就作家而言,他的童年的种种遭遇,他自己无法选择的出生环境,包括他自己的家庭,他的父母,以及其后他的必然和偶然的不幸、痛苦、幸福、欢乐……社会的、时代的、民族的、地域的、自然的条件对它的幼小生命的折射,这一切以整合的方式,在作家的心灵里,形成了最初的却又是最深刻的先在意向结构的核心。”[1]这些生命际遇与互动,既成为迟子建认知世界的窗口,也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人物原型与叙事母题,在后续作品中不断被激活与重构。
(二)个性培育与创作投射
父亲对迟子建的教育秉持着开放包容的理念,他以“溺爱”式的放任为女儿的个性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这种教育方式突破传统规训模式,允许她在自由探索中保持本真自我。即便面对迟子建个性中与传统规范相悖的部分,父亲亦选择尊重而非压制,这种态度滋养着她洒脱随性的创作灵魂。“迟子建那种自由不羁的个性、心直口快的处世方式、自信而倔强的心态无不浸润其父亲的人格精神”[2],父亲独立正直的品格不仅成为迟子建的人格参照,其包容态度更赋予她突破常规的创作勇气,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自由气质与精神锋芒。迟子建在回忆中坦言:“他生前从不约束我,哪怕是我的‘个性’惹他不痛快了。除却‘溺爱’我之外,我相信父亲不愿意遏制我的个性发展,这点我一直对他心存感激。”[3]这种感恩之情不仅指向亲情本身,更暗含对父亲教育智慧的深刻认同。
母亲的包容则展现为另一种情感形态。在岁月磨砺中,母亲始终以温柔坚韧的姿态给予情感支持,其爱意渗透于生活细节之中。《龙眼与伞》中春雪送伞的场景,生动诠释了母爱的隐忍与深沉。即便面对女儿的抵触,母亲仍以静默包容化解冲突,这种情感智慧既展现出传统母性的温柔力量,也为迟子建提供了观察人性、理解情感的鲜活样本。家庭的价值取向与教育模式深刻影响着迟子建的人格塑造与创作风格,在她的成长历程中,父母营造的包容环境,共同构建起的充满弹性的家庭文化空间,成为其自由个性发展的沃土,使她在尊重与理解中形成独特的个性光谱。这种家庭文化基因不仅塑造了她独特的人格特质,更使其在文学创作中转化为对生命本真的追寻、对人性多元的包容以及对自由精神的诗意表达等鲜明的艺术标识,彰显了家庭环境与文学创作间的深层关联。
(三)艺术启蒙与文学生成
迟子建对音乐具有极强的感受力,“琴声如黎明之船,驶入我昏沉的睡眠里,将我照亮。当我睁开眼的时候,琴声还在继续,玻璃窗上弥漫着朝霞,好像朝霞也喜欢琴声,特意从天庭飞来听琴”[4]。迟子建的音乐启蒙始于家庭,《苍苍琴》记录了父亲用小提琴声唤她起床的温暖记忆,父亲的小提琴不仅是她审美感知的起点,更悄然为其文学叙述中音乐性语言技巧的形成埋下了伏笔,成为滋养她独特文风的源头之一。基于对音乐独特而敏锐的感受,她将音乐素养内化为文学创作的独特技巧,“从迟子建小说的叙述语句、段落和情绪的表达上来看,很明显就具有音乐般的滑翔、流动感。她的故事似乎并不是由文字、语句连接的,而是在音乐的感觉中以某种自然节奏的方式向前延伸,连人的思绪也随之沉湎、飘荡于其中。这种令人陶醉于幻想的音乐中的效果,其实可能正是作者个性上倾向和诉诸音乐所导致的”[5]。
劳动作为培育迟子建艺术感知的肥沃土壤,在她艺术人格形成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会唱歌的火炉》中,冬日砍柴拉柴的艰辛劳作,经时光沉淀转化为饱含诗意的生命体验。父亲带领她亲近自然的过程,不仅塑造了其对生活本真的认知,更赋予她捕捉平凡事物中诗意之美的能力。柴火燃烧的声响被赋予“歌声”的美学想象,劳动艰辛升华为对生活价值的深刻理解。这种从日常劳作中提炼艺术灵感的能力,印证了批评家洪治纲的论断:“童年记忆对作家创作的潜在影响,并不仅仅是以经验的方式直接呈现出来,而是从个性心理到艺术思维、从文化观念到审美情趣,深深地左右了作家自身的艺术创造。”[6]母亲的文化实践也为迟子建搭建了审美判断的参照系。《两个人的电影》中介绍了母亲对《红楼梦》的独到见解、对文艺作品的严苛品鉴标准,她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培养了女儿对艺术品质的追求。也正因这份精神层面的深度共鸣,母亲不仅是血脉相连的亲人,更成了最懂她、最能与她共情的知己。
“五四”以后,中国散文挣脱旧文学束缚,迈向个性解放与思想启蒙的进程,作家的创作观念及心理机制发生根本转变。此时期散文以批判封建礼教、呼唤人性觉醒为核心主题,成为知识分子表达自我、批判现实与传播新思想的重要载体。迟子建虽处于和平年代,却继承了“五四”散文关注个体内心的传统。她以童年经验为切入点,挖掘成长中的情感细节,展现亲情对人格塑造的作用,是“人的文学”理念在当代的延续,呈现了个体生命在平凡日常中的精神成长,构成基于人性温暖层面的继承。同时,其以个体生命体验为依托,将宏大文学命题转化为生活细节的诗意书写,既彰显了日常生活场域中艺术启蒙的独特价值,亦延续了“五四”散文的个性表达精神。
二、文化坚守:故园厚土的深情守望
迟子建的文学根系深扎于故园土壤。正如她在《两个人的电影》中所言,她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与故乡、童年及其所热爱的大自然是紧密相连的。北极村,不仅是她创作的灵感源泉,更是瞭望世界、探索人生的起点与永恒归宿。在她笔下,承载地域文化灵魂的自然、充满烟火气的日常场景以及凝聚传承之情的民俗,共同为她带来了独特的生命体验。
(一)作为地域文化根基与灵魂的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作为地域文化的根基之一,对迟子建的创作影响深远。黑龙江奔腾不息,流淌着历史与故事,滋养着两岸生灵,赋予这片土地灵动与豪迈;大兴安岭的森林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物质资源,更是精神支柱。森林中的生物,不仅构成独特自然景观,更蕴含着深厚人文底蕴,带给作家深刻的生活感受和审美体验。《好时光悄悄溜走》一文中,她用灵动文字勾勒出大自然四季的馈赠:春日繁花似锦,花香四溢;夏日果实累累,劳动欢歌;秋日五彩斑斓,如诗如画;冬日积雪覆盖,别样风情。明叶菜、野鸡膀子、水芹菜、鸭子嘴、老桑芹和柳蒿芽等山野菜,承载着她童年的味觉记忆;秋天渡过呼玛河采摘稠李子和山丁子,需要暗暗地与黑熊较量;冬天进山拉烧柴能遇到吃僵虫的啄木鸟,能发现怪异的野兽脚印。与大自然的互动无处不在,对故乡的一草一木热爱之情不言而喻。
现代作家们对于故乡的叙事表现出批判式“背对”和赞美式“面向”两种不同模式,前者如鲁迅、萧红,后者如沈从文、废名,迟子建无疑属于后者。她将对故乡每一寸土地、每一缕清风、每一片雪花的热爱倾注笔端,把对冰霜草木的情有独钟化作眷恋故园的深情厚谊。然而与那些单纯赞叹四季之美的自然散文不同,迟子建不仅描绘自然之美,还会把自然变化与家乡人的生活、命运相连,以文字守护地域文化,坚守心灵的净土。《好时光悄悄溜走》中,她感慨十年以前她家居住的地方那空气是真正的空气,那天空也是真正的天空,屡屡流露出对往昔自然之美的眷恋。她以文字构建的诗意自然世界与当下被现代工业文明侵蚀的自然形成鲜明对照,不时深情回望往昔的天然美好生活与诗意栖居的自然环境。
(二)彰显地域风情的烟火日常生活场景
迟子建散文对民风民俗的描写,虽不及小说中丰富全面,但依然通过方言、生产工具、劳动场景、生活器具、童年乐事等元素,勾勒出了极具东北特色的日常生活场景。在《谁说春色不忧伤》《我对黑暗的柔情》《小说的丛林》等作品中,“划拉、扒拉、拾掇、倒洞、歇脚、好嚼儿、面引子、站干、大草甸子”等极具东北特色的词汇,将读者拉回烟火升腾的东北乡村。《农具的眼睛》《好时光悄悄溜走》《是谁在遥望乡土时还会满含热泪》等文章中,镐头、犁杖、钐刀、耙子、铁齿子等劳动工具,诉说着故乡人民与土地相依为命的故事;起土豆儿、溜土豆儿、拉柴火、架鸡舍、抓猪崽儿等烟火升腾的场景,展现出故乡人民质朴坚韧、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二齿子、维得罗、桦皮碗、铁笊篱、咸菜缸、猪食槽等生活器具,记录着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见证着迟子建的成长足迹。
正如梁实秋眷恋北平传统美食,陈忠实钟情陕西面食,李碧华聚焦香港特色汤圆,汪曾祺描绘江南家常菜,不同地域作家对家乡饮食的执着书写,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呈现载体。迟子建童年的欢乐,还体现在乡村饮食中,《家常豆腐》中,她表达了对豆腐这一寻常百姓家惯常食品的喜爱以及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蚊烟中的往事》中写道:“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这个人拿棵葱,那个人拿棵菠菜,另一个人则可能把香菜卷上一绺,大家纷纷把这些碧绿的蔬菜伸向酱碗,吃得激情飞扬的。”[7]生动的场景描写触动人们内心深处对故乡味道的怀念。《故乡的吃食》一文更是把家乡一年四季的吃食如数家珍地一一道来,无论是高粱米粥、碴子粥、干菜、炖菜等家常便饭,还是春饼、粽子、月饼、腊八粥等节令饮食都各具神采、别具风情。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迟子建见证了故乡的老旧物件逐渐消逝,目睹了传统热热闹闹的家庭生活场景的悄然退场,心底对往昔的怀念愈发浓烈,惋惜与遗憾也油然而生。在《最是花影难扫》中,她理性审视工业化进程对乡土的侵蚀:田产的天然蔬菜被暖棚化肥菜取代,失却自然本味;冰灯在都市繁华中褪去宁静纯粹;空洞艺术品疏远人与自然的距离,感慨电灯代替了蜡烛,永恒的光明也摧毁了窗格里的梅园。她一面缅怀自然真实、情感充沛的旧日生活,一面唤醒读者审慎反思现代文明,警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所滋生的疲惫、迷茫与冷漠的“城市病”,敦促人们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之道。
(三)凝聚传承与怀念之情的民俗氛围纽带
书写故乡是一场探寻精神原乡的漫长征途,迟子建不仅将民俗风情作为审美对象融入文本,更于深层结构中拓展作品内蕴,让故园不仅成为地理意义上的乡愁载体,更成为照见人类生存困境的精神镜鉴。在《房屋杂谈》一文里,木刻楞的原木纹理裹挟着森林气息,外墙上悬挂的干辣椒、鱼干与渔具,诉说着农耕渔猎的民居建筑图景。《马背上的民族》中身着过膝蓝布旗袍的鄂伦春男子,《暮色中的炊烟》中黑色曳地长裙配古铜三角巾的俄罗斯老太太,《听,谁在伐木》中她脚穿的充满乡土气息的棉靰鞡,都生动展现出服饰民俗的民族风情与地域特色。她笔下的春节,更是一幅东北民俗文化怀旧长卷,《故乡的吃食》对腊月宰猪习俗的刻画,展现东北人对美食的热爱、对生活的热忱以及阖家团圆的祥和图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中,小年前后与邻家女孩采办年货、挑选新年饰品的琐事,以小见大,折射出特定时代普通民众的精神追求;《农人的浴室与茅楼》介绍了一年一度的腊月“放水”的习俗;《年画与蟋蟀》生动记述了年前张贴年画的习俗,浓郁的年味儿溢于言表;《冰灯》则讲述了元宵节家家户户摆放冰灯的习俗。这些东北民俗的活态记忆,反映了人类文明转型时期,作家对家园本真与精神原乡的永恒追寻。
当乡土民俗遭遇现代性冲击,她以“文化坚守”为信念,将客观历史转化为带情感温度的回忆叙事,使乡土“神性”在文学中获得永恒。《蚊烟中的往事》里围坐院落晚餐的岁月,《伐木小调》中消逝的风雪与伐木声,都承载着她对故园的集体记忆。迟子建对家园的书写既异于沈从文《边城》剥离矛盾的“乡土乌托邦”,也别于鲁迅《故乡》对乡土痼疾的冷峻批判,而是温情中保持清醒:珍视木刻楞纹理,又痛惜野味被暖棚菜取代;怀念冰灯夜色,亦警惕都市对自然灵性的消解。这种眷恋与反思的双重维度,使其超越单纯怀旧。较废名冲淡空灵的意境更添几分烟火的厚重,比汪曾祺江南风物描摹则多了对现代性侵蚀的隐忧。这种扎根厚土又直面现实的创作姿态,使她构建的精神家园既获得读者广泛共鸣,更完成了对地域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
三、生命哲思:人生逆旅中的精神探寻
迟子建追忆散文将生活体验、情感经历与哲学思考相融合,在自然万象、情感纽带与苦难超越中,构建起充满温度与深度的精神世界。通过对生命本质、情感力量与精神韧性的多维阐释,不仅展现出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更折射出人类共通的精神追求,为读者提供了感悟生命、思考人生的文学范本,彰显出文学作品对生命价值的永恒追寻与深刻表达。
(一)用世间万象承载生命哲思
迟子建深植于自然与生活的沃土,以精妙的艺术手法,将自然万象的荣枯兴衰与人生的生死轮回相勾连,将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创作手法推向哲学层面的深度。她敏锐捕捉自然万象的荣枯轨迹——春草破土的坚韧、秋叶飘零的落寞,将这些此消彼长的自然规律与人生的生死轮回、命运起伏相类比,使自然现象成为解读生命本质的隐喻符号。在《寒色》中,她将北方四季更迭的自然循环,与时光流转、生命荣枯进行镜像叠合。这种融合不仅展现出岁月轮回中故乡风貌的嬗变与个体心境的迁移,更使怀旧叙事升华为对生命永恒与无常的哲学思辨。而在《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中,大兴安岭向阳山坡草芽破土与背阴处残雪未消的细腻刻画,既呈现出自然景观的时空层次,又通过雪与草的意象转换,暗喻时间线性流动与生命周而复始的辩证关系,构建起极具张力的生命美学图景。脆弱易逝与顽强不屈的生命属性形成鲜明对照又相互交织,这种矛盾统一的生命形态,引导读者以更深刻的视角审视并珍视生命历程。
迟子建的创作是一场与生命的对话。她通过对自然与生活的观察与感悟,将生命的哲思与个人的情感巧妙融合,用一个个富有个性和诗意的意象,构建起一个充满温度与深度的文学世界。在这一过程中,故乡的自然景观、人文风貌作为承载集体记忆与个人情感的特殊符号,被赋予了深厚的象征意义。《暮色中的炊烟》里袅袅升腾的烟火,承载着对童年邻里的追忆;《伤怀之美》中冷风中的晶莹树挂,凝结着对恩师的深切缅怀;《灯祭》中年节里温暖而孤寂的灯火,诉说着对父亲的绵长思念;北国纷飞的雪花在《白雪的墓园》中成为思念亡夫的情感载体。这些意象超越了单纯的景物描写,成为集体记忆与个人情感的承载物,她通过文学语言的艺术重构,将抽象的哀伤转化为可感的审美体验,完成了从生活具象到情感抽象的美学转化,使其散文作品既饱含生命哲思的厚重,又流淌着情感温度的诗意。
(二)以情感纽带镌刻生命温度
亲情纽带构成了迟子建追忆散文的基石和核心驱动力。父亲与丈夫的离世重塑了她的情感结构与创作路径,催生出以追忆为内核、以情感为脉络的独特叙事范式。这种基于血缘与婚姻关系的情感表达,经文学审美转化后,升华为对人性光辉的诗意书写。父亲的骤然离去,在迟子建内心深处撕开了一道难以愈合的精神创口,却也促使她以文学为媒介重构记忆。在《腊月的守灵》《父亲的肖像》等创作中,她以克制而细腻的笔触,将父亲的生命轨迹置于时代与地域的宏大背景之下:年少时奔赴大兴安岭的拓荒之举,展现出个体在生存困境中的坚韧与勇气;创业历程中的默默坚守,则映射出传统父性角色的责任担当。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常场景——手工捏制腊梅、山林烤土豆、晨间犬吠相伴的唤醒记忆,在文本中被赋予了超越时空的情感张力。这些记忆碎片经作家的审美过滤与艺术重构,凝结为承载父性精神与价值观念的文学符号,不仅深刻影响着她的人生选择,更成为其创作中持续闪耀的精神光源。
婚姻关系则展现出另一种维度的情感力量。《雪山的长夜》《尼亚加拉的彩虹》《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文章中,她对丈夫的追忆,既包含对其爱岗敬业、勤学上进等人格特质的细腻刻画,也不乏对生活中诗意瞬间的深情捕捉。作者的回忆中,一再出现他们手挽着手、踏着雪无言地走在无人的堤坝上的场景,这种回忆还原了生活本真,将平凡日常升华为永恒的记忆。而“春风能染红唇,能让它像一朵永不凋零的花,吐露心语,在深夜时隔着时空,轻唤你曾爱过的人,问一声:你还好吧”[8],这种隐喻书写,则打破时空桎梏,构建起跨越生死的对话空间,使逝去的爱情重获新生,并转化为具有永恒价值的创作母题。爱情叙事不仅拓展了迟子建作品的情感深度,更通过对生命温度的细腻勾勒,实现了个体经验向人类普遍情感的升华,使文字成为镌刻生命温度的永恒载体。
(三)凭生命韧性跨越精神苦难
迟子建在散文创作领域构建起独具辨识度的美学范式,其文本世界始终贯穿着对生命本真的深度叩问与终极关怀。作家以细腻绵密的笔触勾勒出充盈着人性温度的精神境域,通过对生命价值的多维阐释,展现出对生命存在的敬畏姿态与哲学思辨。基于血缘与情感纽带的追忆书写,不仅是个体情感的宣泄载体,更构成了其创作中深沉厚重的情感基底。当亲人离世这一生命事件发生后,迟子建将现实层面的丧亲之痛升华为文学场域中的永恒怀缅,使死亡叙事成为情感重构与精神突围的重要路径。在《白雪的墓园》《亲亲土豆》等经典文本中,“父亲之死”“丈夫之死”等主题的反复书写,实质是作家对生命终极命题的持续探索。这种书写行为既包含对个体生命消逝的悲怆咏叹,更暗含着对生命超越性的哲学追寻。
从创作风格演进轨迹来看,迟子建早期作品以童真视角展现童年记忆与亲情温暖,呈现出质朴纯净的美学特质;后期创作则因生命阅历的积淀,在文本中注入对时间流逝、生命无常的深邃思考,弥漫着存在主义式的悲凉意绪。荒原落日、飘零黄叶等自然意象群的频繁使用,不仅是地域文化符号的文学转译,更成为作家情感投射与生命感悟的审美载体。在《灯祭》中,墓前点燃的灯盏成为连接阴阳两界的精神媒介,象征着生命意义的延续与升华;《一滴水可以活多久》则以诗意化隐喻解构线性时间观,构建起生命轮回的哲学认知体系。这种将个体苦难转化为文学创作动能的实践,再一次印证了即使在最为艰难的时刻,艺术依然能够成为人们表达内心世界、寻求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
迟子建笔下的生命韧性与精神超越,延续了五四运动以来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创新谱系,与抗战语境下激扬的民族精神形成跨时空对话。以巴金为例,作为革命战争的亲历者,他在“死”与“生”的循环考验中持续完成自我认知、自我发现与自我实现:一方面深刻揭示战争的残酷现实,另一方面以金子般的意志与信念传递对生命的珍视、对家国的挚爱,以此砥砺民心、召唤希望。若说巴金散文以近现代革命史与战争史为底色,书写出感时忧国的精神锋芒;那么迟子建则以日常生命关切为切入点,展现出温润而坚韧的精神向度——二者共同构成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在不同时期的生动表征。尽管所处的历史场域与创作语境截然不同,但作家们在彰显人性光辉、弘扬生命力量的精神内核层面达成了深度共鸣,彰显了不同时期文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职责担当与文化自觉。
结 语
相较于小说与诗歌的虚构性和意象性,散文以更贴近生活本真的形态,将作家的个体经验与时代语境相勾连,从而成为解读作家文学世界的重要密钥。正如郁达夫所言,“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9]。迟子建以独特的追忆式书写构建起个体生命经验与时代精神的对话通道,她的散文将童年记忆、地域文化与生命哲思熔铸为审美意象,不仅实现了对个人生命轨迹的诗意重构,更成为解码其小说创作的精神密码。换言之,这种以散文为载体的追忆书写,不但形成了独特的叙事策略,还与其小说作品共同呈现出鲜明的文本互文性特征。如散文《云烟过客》中对父辈生存境遇的追溯,不仅勾勒出特定历史语境下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更为《原始风景》《花瓣饭》等小说提供了原型叙事的情感基底;散文中反复呈现的东北地域文化符号,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鱼骨》等小说作品中则升华为对生态伦理的哲学思考。这种散文与小说创作的互文关系,印证了追忆叙事作为迟子建文学世界的建构基石,既完成了对生命本真的诗意呈现,又实现了对历史记忆的文学重构。在当代散文创作的精神维度上,迟子建的写作实践彰显出知识分子深沉的文化自觉与坚定的使命担当。她通过重构日常生活经验,在微观叙事中蕴含着宏大的人文关怀:对亲情、爱情、乡情的细腻抒写,既延续了中国散文以人为本的优良传统,又借助怀旧叙事对现代性困境作出柔性回应。在守护地域文化根脉中坚守文化立场,在超越个体悲怆的咏叹中重新确认生命价值。对黑土地的深沉眷恋、对传统和谐生态异化的忧虑、对生命永恒意义的探寻,使其散文创作突破了单纯怀旧书写的局限,升华为对文化传承与生态伦理的深刻哲学思考。这种创作风格既承继了传统散文“文以载道”的精髓,又在当代语境中拓展了散文的精神疆域,为当代文学回应时代命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书写范式。
[1] 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2] 管怀国《迟子建艺术世界中的关键词》,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3] 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文艺评论》2001年第3期。
[4] 迟子建《迟子建散文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页。
[5] 吴俊《追忆月光下的灵魂漫游——关于迟子建小说的意蕴》,《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
[6] 洪治纲《文学:记忆的邀约与重构》,《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7][8]迟子建《也是冬天,也是春天》,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34页,第107-108页。
[9]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