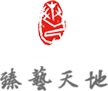
文艺评论
Comments
杨 楠 安 舜
摘 要:中国绘画对“光”的表达历经从隐性认知到显性理论的范式转型。在传统画论中“光”被纳入虚实关系体系,经由黄宾虹、李可染等近现代画家的探索逐步转向自觉性表达。20世纪90年代于志学创造出一系列冰雪画技法,其突破性在于构建“抽象光”理论体系与“光栅法”技术系统双重维度,通过矾墨技法形成的“光”对传统黑白关系范式进行革新。在实践层面,深入剖析“光栅法”包含的三种技法在冰雪画实践中的应用过程,即从观察自然出发,经创造构建和图式生成,最终实现审美意象的转化。“抽象光”理论体系既包含了东方艺术的本体特征,又拓展了中国绘画语言的当代表现维度,从实践角度为中国绘画现代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创作启示。
关键词:中国绘画;“用光”;冰雪画;“抽象光”
“用光”表现方式的探索始终是中国画现代转型的核心命题。传统绘画虽通过“计白当黑”等理念蕴含光的表现,但其表达多依附于笔墨程式,未形成自觉的实践及独立的审美体系。20世纪以来,黄宾虹“夜山灵光”、李可染“逆光变法”等探索,推动中国画“用光”从隐性经验转向自觉的理论构建。本文构建“历史演进—理论创新—技术实践”的研究框架,旨在揭示中国画“用光”语言体系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引发有关中国绘画“用光”表现方式的探讨与研究。
一、中国绘画中“光”表达的历史脉络与现代转型
在自然界中,“光”是抽象无形的存在,需借助物体明暗变化方能被感知。西方绘画通过明暗对比呈现物象的空间感与质感,而传统中国绘画因不拘泥于明暗调子与透视结构,形成了迥异的艺术特征。但在顾恺之《画云台山记》、郭熙《林泉高致》、邹一桂《小山画谱》等典籍与古代画家们的实践中,仍可发现古人对“用光”的独特阐释与实践智慧。
1.传统中国画论中“光”的隐性维度
在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中,虽未曾如西方绘画那般明确指出“用光”的关键意义,但其于不经意间留存了有关自然界中的光线及与绘画“光”运用相关的论述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第一,关于阴阳向背的维度。东晋顾恺之在《画云台山记》中记载“山有面、则背向有影”[1]。著名的中国绘画史论家俞剑华对此阐释道,绘制山景时,需区分向背以表现立体感。北宋沈括于《梦溪笔谈》里评价五代画家董源的《落照图》时指出,其通过山顶明亮石块与周围苔点的对比,营造出夕阳反照的效果[2]。这表明董源在描绘江南山水之际同样运用了“光”这一要素。
第二,关于光影变化的维度。北宋画家李成在《山水诀》提到光所带来的明暗随时间、天气、季节变化[3]。同为北宋画家的郭熙于《林泉高致》中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表示山的明暗变化受日影、季节和天气影响,从而展现出多种形态,可见其对自然光影的细腻观察[4]。
第三,关于阴阳结构的维度。清代画家龚贤于《龚半千课徒画稿》中记载了对于阴面阳面的论述,提到运用皴法时,指出在下方皴而不在上方皴,是为了区分阴面和阳面[5]。清代《芥子园画传》在《山石谱》中针对山石的阴阳面有着更详尽的区分,以“石分三面”的原则,通过“凹深凸浅”表现立体结构与光影变化[6]。
第四,关于光感与中国画关系的维度。曹雪芹曾积极倡导绘画表现光感,但当时未成主流[7]。清代画家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虽承认西洋画光影精准,认为其绘画在阴阳远近方面不差丝毫,却批判其缺乏笔墨意趣,不重笔法,即便精巧也只是工匠技艺,所以不列入画品[8]。邹一桂的理念折射出传统画论对光影的审慎态度。
2.传统中国画作品对“光”的非自觉实践
传统中国画家们虽没有刻意“用光”,但不乏观察光和体现光的画家及作品。有些作品借由笔墨的浓淡干湿、构图的形式差异、氛围的烘托渲染,给予观者视觉暗示与联想,使人们能够觉察到画面上光的存在,具体反映在以下三个层面。

图1 《潇湘八景——渔村夕照图》 南宋 法常 112.6cm×33cm 日本根津美术馆藏
其一,画面中描绘着似有光影效果的客观物象。例如前文提到董源的《落照图》,山顶多画名曰矾头的明亮的石块,颇具光亮之感。黄宾虹曾评价董源的作品,近看时只觉笔墨纵横奔放、起伏不定,远看则是山峦起伏、林木繁茂,村舍或远或近,恰如一幅极其工巧细密的画作。虽然这幅画的真迹已遗失,但通过字里行间的描述,人们联想到西方绘画中的存在显著明度反差及光感变化的画面层次,说明董源的这幅作品中有光感表现的客观存在。
其二,通过刻画呈现出画家的“用光”意识。如北宋范宽的《雪景寒林图》中,山头堆积的白雪隐约发出幽冷光芒,体现了较突出的“用光”意识。南宋法常的作品《潇湘八景——渔村夕照图》(见图1)中,画面右侧倾斜的白光延伸至远峰,重现雨后霁光照射的景象,给观者明显视觉刺激。
其三,画面中呈现创新的光感表达。如清代画家石涛,对自然界的景象予以真挚的体会和领悟,在创作山水画时常常会在山头位置留出明亮且空白的区域,并且用浓墨烘托山顶或山脚之处,令整幅画面既明净光滑又水墨肆意。在他的作品《画山水轴》(见图2)中可见若隐若现的光影穿插于山石树木以及屋宇之间。

图2 《画山水轴》 清代 石涛 154.7×47.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近现代中国画家对“用光”的自觉探索
黄宾虹对“用光”的探索与理论建树,已然突破传统画学藩篱。其言“画有起点,始言光线”[9],“北宋人多画阴面山”[10]等,更独创了“夜山灵光”的表现手法,彰显其对“用光”的高度关注及成熟见解。李可染则更明确地强调画面中受光作用影响产生的明暗变化及层次处理,并且十分讲究画面中明度变化,如用逆光展现林木山峦的层次等。
20世纪80年代初,于志学在创作冰雪画时,探索“用光”以提升中国画的表现力。然而,传统绘画中“光”难以彰显,也缺乏相关技法总结。周学斌也曾于90年代指出,中国画倘若要创新,就需拓展“用光”研究。
综上所述,东晋至明清,传统中国画论与实践中虽隐含“用光”意识,却未将其系统化,原因有三:其一,受制于绘画表现技法的局限;其二,源于传统艺术尚“气”崇“虚”的审美取向,将自然光效主观内化为体感表达;其三,因文化禁忌视阴影为不祥,有悖君子坦荡的意象影响画面美感。在此历史语境中,“用光”始终未能如“骨法用笔”“随类赋彩”般形成完整且独立的学术体系。于志学对“用光”的研究即由此深化拓展。
二、“抽象光”理论体系建构与冰雪画图式革新
中国传统绘画在表现冰雪物象的光影层次及质感等层面存在一定局限性。为克服这些限制,于志学构建了冰雪画“用光”理论体系,实现了视觉图式革新与“抽象光”语言体系建立的双重突破,呈现出冰雪画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视觉效果。从“抽象光”概念、创造理念、对黑白关系的影响三方面的探究,构建了冰雪画“抽象光”呈现的“理论突破—体系生成—价值反哺”的体系模型。
1. 冰雪画“用光”的视觉语言创新——“抽象光”概述
于志学将“用光”分为“具象光”“意象光”“抽象光”三种。他提出,“具象光”以李可染为典型,融合黄宾虹墨法的黑亮特质与西方写实光影体系,强调统一光源下的明暗与层次。“意象光”承袭龚贤等清代画家传统,通过笔墨间隙的空白营造散光效果[11]。而“抽象光”作为于志学的核心创造,以冰雪画为实践载体,通过矾水水痕线形成具象“白线”,既勾勒物象轮廓又呈现逆光效应,开创非光源依赖的“用光”语言系统。
于志学在研习柯罗与毕沙罗的绘画实践中获得启示,通过融合二者绘画艺术的光色表现与中国水墨传统,建构起冰雪画“抽象光”理论体系。柯罗将“光”视觉语言服务于主题意境建构,使光从属于精神表达的理念,深刻影响了于志学的“用光”视觉语言逻辑。毕沙罗的雪景画中厚重雄浑的视觉特质,启发了于志学通过创新视觉语言提升对冰雪的表现力,推动其打破中国传统雪景画荒寒萧瑟意象的范式。毕沙罗的偶然性笔触也为于志学后来创造冰雪画中表现冰雪消融等景象的技法提供灵感。
于志学在创造冰雪画时积极融合了中西方绘画技法,借鉴了西方“用光”体系,创造出“光栅法”,以矾墨技法生成的“白光”构建画面“用光”逻辑。这种“白线”突破传统留白的虚空属性,转化为具有实体功能的视觉符号,支撑起“墨有韵,白有光”的美学主张。抽象光的本质在于对自然光影的辩证转化——通过提炼物象表面模糊光线为明确“白线”,既保留中国画平面特性,又实现逆光效果的意象表达[12]。也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借用光”,是指局部截取自然光影元素,依照画面特定的虚实变化、黑白关系等重组光感。这种局部借用不展现出完全的明暗光影的真实体感,形成无固定光源却充满光感的动态视觉系统[13]。
2.冰雪画“用光”的理论体系生成——“抽象光”的创造理念
随着对冰雪画创造的深入研究,于志学逐渐认为“用光”与用笔、用墨同为绘画核心要素,并构建了“抽象光”的“用光”体系。通过分析其艺术历程与创作实践,可归纳出三大核心创造理念。
第一,中西融合的视觉转化。基于早年中西方艺术的双重熏陶,于志学创造性地结合了中西方艺术两种绘画形式语言。其“抽象光”理论兼具平面性与线造型特征,既保留中国画平面性特质[14],又通过矾水水痕线塑造逆光效果,将西方明暗对比转化为黑白关系。冰雪画中借助矾水水痕线形成的冰雪自然物象的逆光效果即典型的平面性用光。在冰雪物象表现中,他以具象线条凝聚抽象光感,形成一条“白线”,既形成大面积平光照射效果,又通过物象轮廓线维持平面特性。这种转化并非简单嫁接,而是在真实的冰雪中观察所得,进而重新建构的视觉语言体系。
第二,时代精神的视觉表征。于志学冰雪画中“抽象光”的用光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属性。八五美术新潮后的艺术变革期,使我国的绘画冲破了形式的枷锁,画家们逐步领会到与时代共进的重要性。于志学将“用光”问题作为独立的绘画元素进行系统研究,带有清晰的创新特点和时代属性。其创造出表现东北冰雪的技法体系,这一突破性实践于1980年北京画院座谈会上获得潘絜兹、周思聪等多位前辈画家的肯定,对当下时代其他画家和美术工作者有着鼓舞和推动作用。哲学家刘再复先生在《冰雪山水画论》的序言中表示“他(于志学)的名字也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符号”[15],印证了该理念与时代创新的契合。通过构建冰雪画特有的光效语言,不仅拓展了中国画表现维度,更为地域性绘画创作提供了参照方法论。
第三,中国画本体的自律发展。在探索“用光”方面,于志学始终恪守中国画本质规律:以线造型为基础,弱化光源色与环境色影响,将西方透视转化为空间层次。他作品中的“白线”与运用的“雪皴法”等技法在保持笔墨本体的前提下,通过侧锋皴擦营造散落于画面的平光视觉效果,他提出的“透射光”“映射光”等概念则选择性融合了西画元素。冰雪画的“用光”方式既延续了“书画同源”的传统基因,又通过现代转化实现语言体系的演进,其“抽象光”更是遵循中国画自律性,形成具有民族特质的视觉系统。
综上,于志学的“抽象光”理论建构于中国画本体规律之上,提出“继承不是重复、一切在于创造”原则,通过中西视觉语汇的创造性转化,形成兼具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的冰雪画。其创新实践不仅拓展了传统绘画的表现维度,更揭示了民族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发展路径。
3.“抽象光”的重要性——黑白关系的创新构建
于志学在积极探索并创立全新的表现形式之时,逐渐构筑起“白”的体系,进行画面中大量“用光”的全新尝试。他针对“用光”的有关研究与探索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创造出冰雪画后,抑或说其研究的“用光”表现手法是伴随着冰雪画的出现而随之产生的,成为他创造冰雪画时要考虑的一项关键问题,冰雪画出现了全新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生成了“白”的体系。他创造的冰雪画将自然观察与技法革新相融合:通过改良明矾固定剂为调剂媒介,结合对北方雪景光影特征的系统研究,成功实现冰天雪地的视觉转译。他在观察自然景观时想到,在特定光线的照映下,自然界蕴含着黑白对立统一之美。自此,他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对于黑白关系的处理途径,即在物象边缘提炼具有逆光特征的“白线”,通过“矾墨”的浓淡对比映衬冰雪的白,强化冰雪材质的表现力。从而创造出“滴白法”“泼白法”“重叠法”“雪皴法”“排笔法”等技法,将传统中本应留白的“虚”的部分进行“实”的描绘。这种用墨显白的逆向思维,源于其深入自然仔细观察真实的冰雪物象后对南北方雪景差异的深刻认知:南方雪景适宜越画越黑,而北方冰雪则需层层提亮。这种独特的黑白对应关系具有动态转换的辩证特征——于密实处透白,在虚疏处见黑,使得白处显重、黑处见轻,通过对比关系构建画面的节奏感及韵律美。
“抽象光”体系的生成,在理论上重构了传统黑白关系的认知体系;在技法层面实现了冰雪物象从自然观察到艺术图式的转化;在实践维度,为极端自然景观的表现提供方法论范例,将传统虚白空间转化为实体化的表达,构建起基于北方地理特征的黑白关系新图式。这一突破不仅印证了丹纳关于“艺术决定于社会、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学说,更使他提出“用光——创建中国画第三审美内涵”“墨有韵,白有光”[16]等思想主张。王伯敏也曾评价其“冰雪山水为‘白银世界三斗墨’”[17]。
三、“光栅法”在冰雪画中的应用与价值
于志学的冰雪画艺术实践实现了双重突破,在题材维度开创北方冰雪的视觉表现范式,在技法层面建构起“光栅法”为核心的“用光”体系。其作品通过将矾墨语言与“用光”表现手法创造性融合,呈现出晶莹澄澈的视觉特质——白山黑水间流动的光感意象,既延续了中国画黑白辩证的哲学内核,又注入西方造型艺术的科学观察。基于跨文化视觉经验,他认为“用光”是中国画用笔、用墨无法替代的一种新的审美形式,提出“抽象光”的“用光”方式理论框架,并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法体系——“光栅法”。这一技法体系的实践将揭示其如何通过系统性“用光”策略调整审美维度,为极端地理景观的视觉转化提供新的路径。
1.冰雪画的“用光”技法体系建构——“光栅法”
“光栅法”中包含对于“轮廓光”“结构光”“透射光”和“映射光”四种类型的光的表现。在技法运用维度上,“光栅法”中除“映射光”用相对传统的渲染技法表现外,其他三种类型的光均利用冰雪画的矾墨技法表现,即以矾水为调剂,将矾水与墨共同作用在宣纸上,产生不一样效果的水痕线。“结构光”依托“雪皴法”的侧锋皴擦形成肌理,展现冰雪物象自身的结构。“轮廓光”借助“重叠法”中锋叠压,呈现冰雪物象的轮廓。“透射光”则借助“滴白法”中于志学创造的“倒锋用笔”,营造笔与笔穿插之间,前后物象交叠的透明质感(见表1)。
表1 “光栅法”中涉及的三种冰雪画技法
| 技法名称 | 研究时间 | 研究背景 | 技法操作 | 技法与光的关系 |
| “雪皴法” | 1964年 | 由于温度变化形成碎冰晶、雪受到重力拉引,冰雪碎晶有其独特的结构与肌理 | 湿笔多次皴擦叠压,模拟冰雪碎晶结构 | “雪皴法”中的多笔叠压之间出现“白线”,形成“结构光” |
| “重叠法” | 1964年 | 由于多次落雪、积雪后,雪块边缘会出现一层层清晰的结构 | 中锋用笔,笔笔相压(压住前一条线的一半),叠加产生积雪层理 | “重叠法”中笔笔相压出现的“白线”形成“轮廓光” |
| “滴白法” | 1974年 | 由于冰雪消融之时,雪水会顺着冰柱、冰凌等向下自然流淌 | “倒锋用笔”,将笔尖压在纸上,多余淡墨如“屋漏”般向下流淌,仿冰雪融滴动态 | “滴白法”中向下流淌的雪水及冰凌、冰柱等出现透明感,形成“透射光” |
在物象表现维度上,于志学利用一条具象的“白线”凝练抽象的光,建构起四种展现冰雪物象光感的表现体系。其一,“轮廓光”作为冰雪画画面中具有主导地位的视觉形式,借助矾水水痕线形成的“白线”烘托强化雪松、雪包等冰雪自然物象的轮廓,表现其逆光效果[18],也是在冰雪画中光感表现手段中最常用的一种。其二,“结构光”借助矾墨侧锋皴擦,形成多层带“白线”的皴擦结构,凸显冰雪内部复杂结构并营造清冷意境,彰显冰雪独特的美感。其三,“透射光”借助矾墨笔触穿插交叠,凸显冰凌等透明物象的空间穿透性,展现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其四,“映射光”以渲染为主,通常横向用笔,表现水面或冰面波光的动态反射效应[19]。
2.冰雪画“用光”实践——“光栅法”在其作品中的应用
于志学的冰雪画作品《郁雪森森》(见图3)为“结构光”的实践应用,采用平视视角描绘雪景森林。画面借助光与影的相互依存以及透光与不透光的对比,营造出深邃清幽的松树林的氛围及黑白相生的光影效果。值得关注的是,在画面中刻画的树木实际上仅以数株呈现,远山亦不过占画面八分之一的比例。然而他通过黑白对比处理手法,即将远景丛林虚化为“黑”,近景树木处理成“白”,辅以远山逆光效果的“灰”,塑造出密林深杳的视觉纵深感。这种“计白当黑”的造境方式,既通过虚实相生营造出林径幽寂的意境,又以丛林大面积的树与雪构成了恢宏之势,彰显出于志学超尘脱俗的旷达胸怀[20]。

图3 《郁雪森森》 94×102cm 1982年

图4 《琼花清尘》89×68cm 1983年
作品《琼花清尘》(见图4)为“轮廓光”的实践应用,呈现漫天飞雪过后的丛林景致。画面中前景以“白”的形式通过矾墨积染形成厚重雪层,暗示此处刚经历剧烈降雪过程,中景雪松似被前景白雪漫反射光照亮,成为相对“白”的部分,与其边缘“白线”反映的“轮廓光”相互映衬。远景天空采用明度渐变处理,两侧较暗,中部较亮,既暗示云层裂隙透光的自然现象,又营造出雪后初晴的空气澄明感。树林深处以虚化的 “黑” 表现视觉纵深感,不仅强化了画面的空间层次,更赋予作品以静谧平和且神秘的氛围。

图5 《静谧森林》 71×44cm 1982年

图6 《春融》 97×60cm 1988年
作品《静谧森林》(见图5)为“结构光”与“透射光”的实践应用,表现出月光下挂满冰凌的密林丛的景象。画面中,半透明冰凌的叠加与穿插形成了“透射光”,圆形光域与方形丛林形成鲜明对比,其构成的几何图式隐喻道家“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将光影转化为哲学观念的视觉载体。这种布局不仅是视觉呈现,更是“光”的运用与象征性符号及语言结合的创新尝试,有效拓展了平面型用光的表现形式。
1988年于志学创作的冰雪画作品《春融》(见图6)为“透射光”与“映射光”的实践应用,通过中轴分割形成上下对称构图,诠释春日冰雪消融的时空叙事。上半幅以“滴白法”呈现冰川融化的透明质感,矾墨的自然流淌与笔触交叠产生“透射光”效应,使观者得以穿透冰凌窥见后方雪山,形成冰川在光照射下泛光的氛围。下半幅作品运用“映射光”技法,以重墨分层渲染水面倒影,通过虚实相生的笔触处理,展现水面经光线反射出的冰川未完全消融的混沌状态,凸显 “春融”的意境和主题。
3.冰雪画“用光”的审美意象——“光栅法”的审美价值
于志学冰雪画的“用光”实践展现出了双重审美价值体系,既实现了对物理光的转译与建构,又建立了对冰雪物象“冷逸之美”的审美意象。通过《郁雪森森》《琼花清尘》《静谧森林》与《春融》四幅画作不难发现,画面中流动的“抽象光”不仅体现光的自然属性,促进冰雪物象的质感表现,更通过营造清冷澄明的意境,实现从自然观察到审美感知的美学跨越。这种独特的审美创造来自他对冰雪物象的独特感知及视觉经验。他通过矾墨语言将北方冰雪晶莹、透射、折射的物理特性转化为“冷逸”的审美视觉表征,在“冰雪美学”的范畴内开辟出“冷中见暖”“静中寓动”的辩证表达路径。
冰雪画的“冷逸之美”本质上是对传统北方冰雪审美范式的解构与重构。于志学以“光栅法”为媒介,消解了传统的厚重、苦寒、凝滞的视觉定式,代之以冰雪世界轻盈的、空灵的意境营造。他专注于表现北方冰雪景观的博大、壮阔、美妙与璀璨,由此形成的“冷逸”的“辉光”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北方冰雪的消极审美认知,更通过“春”与“暖”意境的隐形表达,建构起冰雪世界内在旺盛生命力的审美体验。
于志学创造出的这些表现光的形式语言具有突破的审美价值。在理论建构层面,他认为“‘光’是中国画第三审美内涵”,提出“五品光”的分类方式,分别是玄光——幽邃的墨韵逸光、辉光——矾墨透射的白光、幻光——若隐若现的不定光、冷光——冰雪反射的静态寒光、意光——无光的意象投射[21]。在技法层面,通过“光栅法”实现将光影现象转化为可操作的笔墨程式,为北方冰雪物象提供了难得的表现经验。这种创造不仅拓宽了北方冰雪的艺术表现维度,更为日后冰雪画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实践基础[22]。
结 语
中国绘画的“用光”体系具有历时性演进特征,本质上是视觉认知范式与美学价值的双重变革。从魏晋到明清典籍中的阴阳向背、明暗结构,及至近现代对“用光”的创造性表现,折射出中国绘画“用光”从非自觉表达向自觉独立的审美维度的转型。在此进程中,于志学的冰雪画创造具有两项突破范式的意义,其一,他提出的“抽象光”理论,通过跨文化融合,将传统水墨的平面性与西方造型的立体性进行创造性转化,建构出兼具民族特性和现代性的“抽象光”体系,创新构建了中国绘画的黑白关系。其二,他建构的“光栅法”技法体系实现了矾墨语言对光影层次的程式化转译与表达,完成从自然观察到文化意象的三重转化。这种创造不仅推进其“墨有韵,白有光”的视觉新主张,更通过“冷逸之美”的审美意象转换,将冰雪意象从苦寒禁锢升维至生命张力的审美感知。中国绘画“用光”表现方式的现代性建构,正需在这种传统绘画与现代形式创生的张力中,实现本土美学与世界艺术的创造性对话。
[1]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韩放校,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2] [宋]沈括《梦溪笔谈》,侯真平校,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25页。
[3] [4] [宋]郭熙《林泉高致》,周远斌点校,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第26页。
[5] [清]龚贤《荣宝斋画谱 古代部分 1 清·龚贤绘课徒画谱》,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6] [清]诸升、王质、王概等《芥子园画传》,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年版,第51页。
[7] 胡德平《曹雪芹的“画论”及其时代背景——从中西绘画艺术交流的一组图画谈起》,《曹雪芹研究》2017第2期。
[8] [清]邹一桂《小山画谱》,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页。
[9] 黄宾虹《黄宾虹画语录图释 第2版》,王伯敏、钱学文编,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
[10]汪己文《宾虹书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11]杨宪金《中国画水墨艺术研究中心编. 水墨六》,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67-68页。
[12]于志学《创建中国画第三审美内涵——中国画用光》,《东方艺术》2003年第4期。
[13]刘春燕《光在中国画中的应用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2年,第26页。
[14]王海滨《当下中国画创作中的“用光”问题探讨》,《美术研究》2019年第6期。
[15][19] 章华、余式晖《冰雪山水画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页,第139-142页。
[16][法]伊波利特·阿尔道夫·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5-56页。
[17]王伯敏《黑宾虹,白志学——读于志学的冰雪山水》,《东方艺术》2003第2期。
[18]韩昊《中国山水画中光艺术与笔墨的关系》,《文艺评论》2023年第3期。
[20]杨楠《于志学冰雪画表现研究》,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23年,第31-32页。
[21]于志学《墨有韵 白有光》,《美术观察》2000年第7期。
[22]卢平《中国冰雪画在白俄罗斯反响空前》,《文艺评论》2007年第1期。
(作者单位: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