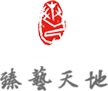
文艺评论
Comments
郎春艳
摘 要:萧红短暂的一生漂泊多地,文学思想深受地域文化与生活经历的影响。在哈尔滨,萧红深受左翼文艺思潮的熏陶,形成具有“在地性”特征的审美经验;在上海与东京,孤寂的生存境遇使其突破以往阶级、贫富的二元式建构人物关系的创作形式,开启新的叙事范式;在全面抗战时期,她辗转于武汉、重庆等地,抗战叙事逐渐从战争的宏观描写转向个体生命的观照,呈现“人道主义”思想;香港是她漂泊生涯的最终驿站,也成就了她文学创作的高峰,作品融合“反思”“启蒙”“救亡”的多元思想,充分彰显萧红文学思想的成熟与深化。
关键词:萧红;在地性;人道主义
20世纪初,社会动荡与变革并存,鲁迅、胡适等先觉者对国内时局的积弊痛心疾首,怀着“别求新声于域外”的渴望,跨越国界,探寻异域的新知与先进思想。与此同时,诸如“子君”“涓生”式新青年群体,追求内在精神自主与外在情感解放,力图挣脱传统家庭的桎梏。他们的人生抉择,是个体对自由的向往,但在特定历史语境下,主体意识觉醒在解构传统文化的同时,必然生发生存层面的漂泊境遇。
当“漂泊”成为现代主体不可规避的宿命时,萧红的人生经历恰恰构成五四时期女性漂泊命运的典型范式。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女性作家,萧红漂泊的生命轨迹恰好处于多个文化转捩点。萧红短暂的一生辗转于哈尔滨、上海、东京、武汉、重庆、香港等诸多城市,这些城市既是地域空间上的漂泊驿站,更是文化交融与碰撞的“见证者”。这种跨域的生存体验,将个体遭际与社会现象、个体命运与国家前途相互联结,使个人化叙事与民族命运在漂泊过程中产生多重对话,最终使萧红成为具有文化间性的时代作家。基于此,本文通过考察萧红从异乡到异乡的地域漂泊轨迹,呈现地域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勾勒萧红文学思想生成的脉络机制。
一、哈尔滨:“在地性”的左翼思想
以“哈尔滨”为观照视角,萧红“所有的叙事动机都在这里萌动,以后只是生长和展开的文体”[1]。显然,创作根性表面,哈尔滨的“存在”有其内在且不可或缺的意义。作为文化异质性的聚合空间,彼时的哈尔滨以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为萧红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生长空间。在时间维度上,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交融;在空间范畴内,宗教文化、俄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多重渗透。这一切皆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文化生态系统中丰富文学叙事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多元共生的文化语境中,萧红得以完成世界观与艺术观的构型,形成了“在地性”的审美经验基底。
得益于时代的风气,17岁的萧红到哈尔滨求学经历成为其思想启蒙的关键,更为命运的“转折”提供必要的条件。“20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2],经历软禁、流浪、身怀六甲被遗弃等诸多遭遇,间接地反映萧红此时“个体自由”革命理想的失败。但是,危机就是转机,正是“个体自由”革命遭受挫折之后,萧红遇见萧军,走上左翼文学的道路。显然,作为萧红文学生涯的引导者,萧军的勇于直面历史,敢于直言不讳,为受压迫阶级挺身而出的左翼言论,如长春《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发表的《一封公开信——致全满洲国爱好文艺及青年文艺工作者》(1933年7月30日),影响着萧红初期的创作思想,但哈尔滨复杂多变的文艺生态环境同样构成重要因素,共同生发了萧红文学中“在地性”的左翼思想特质。
彼时,“受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历史因素的影响,以哈尔滨为代表的东北地区成为中国较早接受俄苏文化思想影响的地区之一……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受着激荡昂扬的俄苏革命文化氛围,东北知识分子正接受了左翼思想的传播”[3],且“在当时认同和运用左翼话语是表明知识分子道德精神立场”[4]。在此文化态势下,左翼文人通过组织文艺活动、建构契合哈尔滨现实需求的左翼文化空间,将分散的进步力量整合为具有“在地”特质的文学场域。于萧红而言,哈尔滨殖民现代性所衍生的多元文化生态,使左翼道路选择成为必然性,并在萧军的引导下,她最初接触的哈尔滨进步文学青年社团“牵牛坊”的经历,进一步强化其对左翼思想的认同,从而更加坚定最初的文学追求和信仰。
同时,由于东北地区独特的地缘位置与复杂的政治局势,尽管东北文坛在新文学的发展进程中相较于关内地区略显滞后,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文学革命的萌芽阶段,“普罗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念已悄然出现,在“1930年代,东北地区普罗文学风气更浓,一扫以往颓靡悲观的文坛风气,把反映东北人民疾苦作为创作方向”[5]。萧红漂泊无定、生活困顿的境遇,使其深刻体会到底层民众生活的悲苦,而这种生命体验与左翼文学“反映东北人民疾苦作为创作方向”的理念形成强烈共鸣。因此,早期文学创作思想,既根源于萧红的感性经验中,又是创作方法论的理性自觉。所以,在“1933-1934年,罗烽、金剑啸、白朗等人受党的指派,为配合当时的左翼主潮,与进步作家萧军等,先后在《大同报》《国际协报》上创办《夜哨》和《文艺》,开辟了以底层劳苦群众命运和阶级反抗等左翼题材为主的进步文学阵地,萧红多数早期作品都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6]。
此外,《商市街》虽然在上海完成,但叙述的是“我”和三郎在哈尔滨时期的生活片段。若将《商市街》置于萧红在哈尔滨的生活背景中进行考量,我们发现,在《商市街》中,萧红自指为“穷人”,将“穷”的生活境遇和内心痛苦具象化呈现,而“穷人”身份的建构又与左翼文学“反映东北人民疾苦作为创作方向”的理念契合。因此,萧红置身《破落之街》的深处,视角触及都市生活的底层肌理,亲身体验《饿》《患病》《最末的一块木柈》等苦难生活,而“饥饿”“疾病”“贫困”作为三重能指,共同指向都市底层的生存真相。欧罗巴旅馆、公园、影院等都市景观的消费符号,皆与主人公形成结构性区隔,“中央大街的南端,人渐渐稀疏了。墙根,转角,都发现着哀哭……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7]。
显然,在哈尔滨时期,萧红“左翼思想”的生成机制,无论是基于30年代初北满地区左翼思潮的意识形态氛围的形成作用,抑或是作为“穷人”作家深受生存困境逼迫的主体性回应,都不可争议地揭示出地域文化与主体境遇在特定时空中的辩证融合,使此时期“左翼思想”带有显著的哈尔滨“在地性”审美特质。
二、上海—东京:突破“二元式”思维的“寂寞”思想
以“上海”和“东京”为观照视角,它们是萧红文学创作思想转变的关键节点。初到上海,萧红通过《小六》与《商市街》的创作,对早期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审视和内省,而后陷入创作焦虑的状态。尽管萧红因《生死场》成名上海,终结“悄吟时代”,开启“萧红时代”,但创作于上海的小说《手》《桥》《马房之夜》,仍然未能摆脱此前的“阶级”“贫富”“等级”二元对立的叙事范式。及至东渡日本,跨文化语境中的孤独生存生发“寂寞”的创作,使萧红突破此前的创作困境,在《家族以外的人》《牛车上》等文本中实现叙事形式的突破。
综观上海时期的生存状态与创作轨迹,萧红面临着情感波折、物质困境与创作瓶颈的多重压力。可以说,最早察觉到萧红在上海面临小说创作困境的是鲁迅。在1934年12月6日,鲁迅致萧红和萧军的信件中谈及道:“一个作者,离开本国后,即永不会写文章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说来。”[8]首次揭示萧红初抵上海时,面对复杂的文化背景,尚未找到适合自身的写作路径。此后一个月,鲁迅在另一封信中又提及:“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9]从鲁迅致二萧的两封信件中,我们可以洞察到,萧红在抵达上海后的两个月内,没有新的作品问世。次年初,小说《小六》(1935年1月)创作完成。同年,《商市街》创作完成,萧红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视角,直面并揭示自身生存层面的诸种困境。1935年9月19日,鲁迅给二萧的信中写道:“久未得悄吟太太消息,她久不写什么了吧?”[10]根据鲁迅书信的时间节点推断,在1935年9月之前,萧红仅完成《小六》和《商市街》的创作,而《商市街》的创作是在同年5月完成。因此,鲁迅在信中所言“她久不写什么”,应该指涉的是除了《商市街》之外的小说创作。直至萧红去往日本,她的文学创作除了零散的散文、诗歌之外,小说创作仅有《手》《桥》和《马房之夜》。
诚然,萧红此时期的文学创作,在数量和深度上皆有待提升,虽不能规避与萧军情感矛盾的影响,但自述:“自己的文章写得不好,看看外国作家高尔基或者是什么……觉得存在在自己文章上的完全是缺点了。并且写了一篇,再写一篇也不感到进步……”[11]直接反映出萧红对文学创作的不满。基于此,文本细读,我们发现《手》《桥》《马房之夜》仍将矛盾冲突嵌入贫富、阶级的二元叙事话语,沿袭早期人物关系建构的路径。因此,若暂置情感因素,不难发现,萧红已陷入创作的瓶颈,这不仅是创作手法的困境,更触及对左翼现实主义方法论的反思:如何突破阶级叙事话语?如何重构人物关系的多元向度?
日本时期是萧红创作突破的转捩点。萧红前往日本时心情低落,抵达后亦没有多大改观。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发烧、头疼、肚痛等症状几乎成了生活常态。在病痛与思乡的双重折磨下,萧红“孤独得和一张草叶似的”[12]。然而,恰恰是这份“孤独”“寂寞”的生存体验,激发创作的自觉。萧红开始有意识地回望故乡与童年,通过对故土经验的重构,无形中解构了左翼文学中“阶级”“贫富”二元叙事形式。1936年8月27日,萧红致信萧军:“现在要开始一个三万字的短篇了。给《作家》十月号”[13],四日后(8月31日)的信中又兴奋地宣告:“不得了了!已经打破了记录,今已超出了十页稿纸。我感到了大欢喜”[14]。这篇在五天内完稿的作品便是《家族以外的人》,而且萧红“自己觉得写的不错,所以很高兴”[15](1936年9月4日信)。新的书写范式缓解了萧红的创作困境,亦使心灵得到慰藉。随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萧红陆续地完成了《家族以外的人》《牛车上》《王四的故事》等作品。
通观这几部小说,“家”是隐含的主题。在小说中,主人公对“家”的纯粹、圆满的渴望与预设,与现实生活中的战争、死亡,以及诸种人为的不可抗拒力量,皆将人物推向“无家”的境地。显然,理想中“家”的温情与现实中“无家”的困窘,二者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主人公对“家”的期待与现实的残酷对比,令这份期待不断遭受撕扯,“这种撕扯见证了偏僻的人生的存在”[16]。由此可见,萧红在日本时期的文学创作,为人物设定的“家”与“无家”的生存境遇,突破了早期二元阶级叙事话语。此时,“家”的所指完成转换,作为文化符号的“阶级”“贫富”对立,被置换为存在境遇中“家”的困境,标志着萧红文学思想的重要转变。
三、武汉—重庆:“途中”文艺的“人道主义”思想
全面抗战时期,萧红的地域迁徙达到漂泊生涯的巅峰,形成“人在旅途”的典型漂泊图景。战时生活的亲身体验,直接促使萧红在文学创作中不断调整并深化文学观念,抗战叙事从聚焦战争本身转向关切战争背后个体“人”的命运,呈现“人道主义”思想。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唯有将这一时期地域迁徙的轨迹串联起来,才能更好地厘清萧红“人道主义”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七七事变”后,战火迅速蔓延至上海,萧红在“八一三”战火中随文化界同仁撤离,1937年9月抵达武汉。在流亡途中,萧红亲历战火,使其从战争的“旁观者”转变为“亲历者”。同时,受战事的影响,诸多党政机关、文艺界人士及出版机构等纷纷向西迁移,使武汉成为抗战初期的文化中心。在动荡不安的外部环境压力下,战时文艺动态迫使文艺创作突破既有的话语范式,承担文艺使命与责任。在这种文化生态语境下,萧红积极参与抗战文艺的交流与创作,逐渐形成具有生命政治特点的创作观念,将战争对个体生命的戕害转化为文学内在张力。
1938年1月27日,萧红与萧军、聂绀弩、端木蕻良等前往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随着战争局势的紧张,民族革命大学决定战略转移至晋西南乡宁一带。此时,萧红与萧军在去留问题上产生根本性分歧。最终,二萧分道扬镳。学界对萧红未前往延安的动因存在诸多揣测,细加梳理,实则可归结为双重因素:一是情感纠葛的复杂性,即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三者之间的情感关系,或许成为其决策的考量;二是萧红个人的政治立场与态度,或许是其最终选择的关键。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西战团、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浓厚的政治氛围让萧红某种程度上不适应,但并未达到完全排斥。实际上,萧红没有选择延安的意向,在与萧军分手之际便已隐约呈现。二萧的分开,表面上看似乎是两个人情感的结束,实则是“人生抉择的差异”[17],是萧红自主人格的形成,是成长为独立个体的“萧红”。
基于此,当萧红重返武汉时,文学观念愈发成熟,逐渐形成基于生命本位的“个人化”抗战文艺观。她经常参与《七月》同仁的座谈会,针对抗战文学发表见解:“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18]。在“抗战高于一切”的强烈呼声下,众多作家纷纷响应抗战文艺的号召,投身于抗战文学的大潮中。然而,这股热潮亦导致当时许多的抗战作品陷入公式化、概念化、形式化的窠臼。相较之下,萧红的“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的创作理念尤为独特。1938年5月,萧红创作散文《无题》,通过“在西安八办设在通济南坊27号的招待所住过一段时间”[19]的亲身经历,消解英雄主义叙事。在散文中,萧红在描绘一位失去一条腿的女战士成为众人瞩目的英雄的公共话语之外,联想到这位女战士日后作为母亲将承受的精神创伤。显然,萧红敏锐地捕捉到被宏大叙事遮蔽的细微之处,站在尊重与关怀生命的立场上观照周围的人和事,从而呈现鲜明的“人道主义”思想。
1938年8月,武汉沦陷后,萧红又一次漂泊流亡。同年9月,她辗转陪都重庆。在重庆生活的一年又四个月期间,她建构了一个“抗战的场域”,深入战时社会的肌理,关切战时生活中“人”的生存状态。同时,在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背景下,萧红进一步反思国民性,并将这一主题延伸至香港时期的文学创作。彼时的重庆,“一切文化活动……集中于抗战有益的这一焦点……一切文化活动都充分大众化”[20]。显然,所有的文化活动皆以服务抗战为目标。因此,诸多作家以抗战为背景,创作许多杰出的文学作品,而萧红同样在抗战的硝烟中汲取素材,但有别于其他作家,努力突破战争叙事的既定框架,揭示抗战背景下普通民众艰难的生存状态,如小说《逃难》《莲花池》《山下》《旷野的呼喊》《黄河》,散文《牙粉医病法》《滑竿》《长安寺》《放火者》《茶食店》《林小二》等。其中,《放火者》(后改名为《轰炸前后》)是萧红于1939年6月9日创作的纪实性散文,记录了从5月1日至5月25日期间,日本飞机对战时重庆大后方轰炸的过程,真实地记录轰炸后城市的满目疮痍、民众惨不忍睹的哀嚎。其中,1939年的“五三”与“五四”大轰炸的场景,亦被记录在此文。
诚然,萧红关于战争的书写,战争图景是文本表征,对战争中“人”的全面观照则是创作目的。她凝视战争阴霾下苍凉、坚韧的人生图景,从而揭示战争中脆弱又顽强不屈的生命力,如阎胡子的憧憬(《黄河》)、李妈的期待(《朦胧的期待》)、陈公公的悲痛(《旷野的呼喊》)、林姑娘的忧伤(《山下》)、保育院难童的孤独(《林小二》)等,而这些人物形象亦共同构成战争创伤下个体存在的症候群体,印证着“战争对人的伤害或扭曲,并不止于肉体,而是涉及人的思想;战争亦不止于影响年青力壮的英雄,亦涉及幼弱的孩童”[21]。此时,战争叙事指向“生命存在”的追问:当战争的硝烟散去,人们将如何生存?又将如何调适心态,去抚平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这种调适是否可能实现创伤救赎?
总之,在全面抗战时期,萧红有意淡化战争与革命本身的直接意义,进一步思考战争与“人”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呈现战争对“人”生活的影响,以及“人”在战争下心理、精神和命运发生的改变,彰显鲜明的“人道主义”思想。
四、香港:“反思”“启蒙”“救亡”叠合的文学思想
以“香港”为观照视角,是萧红漂泊生涯的最终驿站,既是文学创作的艺术高峰,更是文学思想多元融合的时期。在香港的两年时间里,萧红创作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短篇小说《北中国》《后花园》《小城三月》,哑剧《民族魂鲁迅》以及4篇散文。综观此时期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创作理念、表现形式及创作内容,皆发生显著的变化,鲜明地呈现“反思”“启蒙”与“民族主义”嵌套叠合的文学思想特征。
有论者认为:“区分作家的前后期,一度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往往以作者思想的‘进步’转变作为划分其作品前后期的依据,同时潜在地以思想的进步与否对应作品评价的优劣。即转变前的作品是‘有局限的’,而转变后的作品是‘进步’的、‘光明’的,往往也暗示着艺术上的成熟和完美。……毫无疑问,这种做法以先在的政治评判为依据,带有相当大的人为因素和武断色彩,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22]相较于当下文坛对萧红香港时期创作的高度评价,彼时的文坛态度则颇为严苛,其中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提出的“寂寞”论尤为引人关注。他认为“蛰居”的萧红是万分寂寞的:“在一九四〇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做过斗争的人,而会‘蛰居’多少有点不可理解。”[23]“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24]从整体而言,茅盾的评论紧密贴合艺术直觉,准确地把握了《呼兰河传》的抒情特质。然而,身为左翼批评家的茅盾,受政治立场影响,对萧红作品评价陷入褒扬与苛责的悖论。这种在政治意识下产生的评价偏见,给《呼兰河传》带来长久的负面影响。显然,一个作家思想的“进步”与否,直接关联着对作品艺术价值的评判。如果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重返历史现场考察萧红香港时期的生活境况与创作实践,便不难发现,此时期的文学作品呈现“反思”“启蒙”“救亡”三种思想相互渗透、彼此交融的特点,而这一思想特征,彰显了萧红香港时期文学创作思想的成熟与深化。
首先,“反思”思想。“40年代特殊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环境,所带来的作家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生命体验、心理、情感方式……的深刻变化,并最终导致了写作观念、形式的深刻变化。”[25]毋庸置疑,萧红的“反思”思想与战争背景息息相关。早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期间,身处上海旋涡中心的萧红,以“在场者”视角创作了《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火线外》等直击战争本质的作品。同年11月,她又创作了《一条铁路底完成》《一九二九年底愚昧》,两篇作品均以“回忆”的叙事方式,重审自己学生时代参加东北爱国护路运动的经历。文中不乏以“愚昧”“混蛋”的字样,评价学生时代的革命激情,“反思”意味极为浓厚。值得注意的是,两篇作品的创作背景正值“八一三”事变后一系列学生运动。这种时空叠合使萧红具有双重视角,既观察“当下”学生运动的同时,又反观自己学生时代的经历。可见,萧红的反思思想已突破简单的经验否定,上升为对革命激情的自省式批判。这种批判意识在全面抗战时期凝练为“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的文学理念,及至香港时期得到进一步延展与深化,《北中国》和《马伯乐》等力作,皆呈现战争背景下“躲警报姨娘担心儿子”式的日常生活。同时,“反思”思想直指“五四”启蒙的不彻底性,如散文《骨架与灵魂》,小说《北中国》《小城三月》。其中,《北中国》中的耿大先生是“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命运写照;而《小城三月》则通过描写“翠姨”与“我表哥”之间单向度的爱情悲剧,建构多维叙事话语,反讽了所谓启蒙家庭宣扬的平等、自由等理念,在实际生活中的空洞与名不副实。
其次,“启蒙”思想。笔者认为,萧红一贯坚持“国民性改造”的立场,并非茅盾所误解的那般,认为萧红与“生死搏斗的大天地”[26]相隔绝。事实上,萧红一直延续鲁迅“精神奴役的创伤”的文学精神,认为不彻底根除国民的愚昧思想,不利于抗战的顺利进行。基于此,在“启蒙”思想的观照下,《呼兰河传》《马伯乐》堪称典范。前者以“大泥坑”“看客”等隐喻系统,揭示“愚昧而不自知”的乡民集体无意识的生存状态,既是对“国民灵魂”的深入挖掘,更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一次透彻批判。未竟之作《马伯乐》中,马伯乐的软弱、自私、苟安、空虚、装腔作势的形象,以及“真他妈的中国人”的口头禅与“万事总要留个退步”的人生哲学,构成启蒙失败的寓言化书写。萧红借助“马伯乐”的形象,对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进行辛辣讽刺,尤其是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实际上,萧红的“启蒙”思想始终贯穿于文学创作始终,只是在不同时期呈现程度各异,到了香港时期达到批判强度的峰值。
最后,“救亡”思想,亦即“民族主义”思想。笔者认为,萧红在香港时期的文学创作之所以达到艺术高峰,关键在于她将多元文学思想巧妙融入于同一文本之内,呈现较高的造诣。前文论及的《马伯乐》便是典型,在国民性批判的叙事中,蕴含着“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想。马伯乐在战难下被逼迫的“逃”,以及对逃难中“日常生活”的细腻描绘,呈现抗战时期“人”的艰难生存状态。同时,在逃难过程中,马伯乐几乎触及了抗战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而全面展现战争阴影下人们的恐慌与迷茫。此外,萧红多次参加反日活动,先后在几次重要的宣言中郑重签名,这足以表征她对独立、解放等“民族主义”问题的关切与认同。同时,通过《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等文本,将“九一八”事件的历史创伤转化为民族救亡的精神动力,亦标志着民族主义思想从政治诉求向文化认同的深层转化。
显然,香港时期的萧红,看似“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27],但这一表象性状态不能概括其生活全貌,通过她的创作实践与社会活动的考察,可见文学场域的丰富性,不仅包含对战争的反思、“五四”启蒙的重审、“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更有对时代、民族命运的关切。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萧红在香港的文学思想性一直被忽视和遮蔽,唯有回到“历史现场”,将历史语境、文学叙事和思想变革等多重因素综合考量,方能揭示香港时期文学的现代性价值。
总之,萧红的人生际遇与文学创作是一个动态交互的过程。从异乡到异乡的地域迁徙,是萧红漂泊的城市地图,亦是文学地图,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勾勒出萧红文学思想的生成机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存在,萧红文学不仅担起个体经验与历史语境的对话之责,更在《呼兰河传》《马伯乐》等经典文本中完成对民族精神的美学建构。毋庸置疑,萧红的文学创作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内涵,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蕴和社会价值。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金项目“新时期乡村变革视域中的知青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18-KYYWF-1278)阶段性成果]
[1] 季红真《萧红留给我们的遗产》,《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2] 《萧红全集》第三卷,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3][5]谢纳、林静怡《左翼的流亡:东北作家群的革命情结与家国情怀》,《当代文坛》2020年第6期。
[4][6]高艳丽《“重回历史现场”与左翼文学研究——兼谈都市空间的压迫、弃子之痛与萧红左翼的选择》,《文艺争鸣》2012年第12期。
[7] 《萧红全集》第一卷,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8][9][10]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第138页,第255页。
[11]《萧红全集》第四卷,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页。
[12][13][14][15]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第24页,第33页,第39页。
[16]文贵良《〈呼兰河传〉的文学汉语及其意义生成》,《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17]季红真《萧红全传——呼兰河的女儿》,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第403页。
[18]胡风、萧红等《现实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记录》,《七月》1938年第3集第3期。
[19]袁培力《萧红年谱长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92页。
[20]郭沫若《抗战与文化》,楼适夷主编《大后方文学书系第1卷:文学运动》,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页。
[21]陈洁仪《现实与象征:萧红“自我”、“女性”、“作家”的身份探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22]李向辉《大时代中的个人写作——兼论萧红的文学思想和作品分期》,《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3][24][26][27]茅盾《〈呼兰河传〉序》,《文艺生活》1946年第12期。
[25]赵园、洪子诚、钱理群等《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